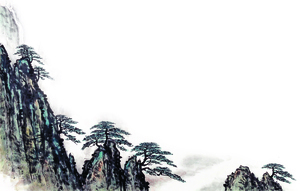笑笑心下緊張,都怪這人太重,否則,她早就跑掉了。
老闆娘因昭雪之事,本就十分不滿,現又跑了個準頭牌,哪裏肯輕放,一路豁出老命,緊追不捨。轉了幾個胡同,笑笑也支撐不住,心想這個老太婆怎生這樣固執,害得自己大半夜揹個廢物滿城亂跑,心下又可氣又可笑。
老闆娘可沒有心情,轉了個彎,見人從房頂上下來,便直衝上去。突然,一陣大風猛然襲來,吹得老闆娘進步不得,大風過後,隱隱一人,攜羽帶紗,風姿綽約,背影姍姍,衣袂飄飄。只見她左手持腰,右手做阻攔之勢,聲柔腔正,道:
「你看我比之她,若何?」
說罷,迴轉身來,纖腰扶柳,淡掃蛾眉,笑靨流轉,青絲曼舞,質麗脫俗,別有氣韻,看得落雁閣的老闆娘,一時失神。
話說昭雪被趕出落雁閣,形單影隻,好生淒涼。正難過間,只覺身子一倒,置身軟轎之內。幾次欲起身,皆被人推擋回來。幽閉的空間,未知的目的。絕望無助,只能讓眼淚流淌。
忽然轎簾掀開,有人道:「哭甚麼!」聲音好生熟悉,昭雪抬眼望去,竟是納蘭,轎子亦不知何時停下的。眼神迷離間,被人拉扯起來,走了一段路,投入一間屋子。昭雪哭了許久,只覺氣力漸竭,便斟了桌上的茶來喝。便才看清身處之地,是一間雅室,桌上放著一件棕色斗篷、圍棋和一幅畫。打開來看,原來是她心愛的泉潤墨竹圖,恍然明白:原來蓬門不是被高義薄所拆,真是錯怪他們了。
翌日清晨,昭雪披了棕布斗篷,行至院中。繞了半個時辰,也沒見半個人影。遠處林間堂前,隱隱透出白色紗幔,甚為肅穆,便走過去。朱門高大,白紗曼揚。昭雪扶門進去,見那人站在堂前,默然對著案上靈位。
昭雪走近一些,見到靈位上的名字,心下一驚,脫口而出:
「沒想到,你也……」
「生死有命,不必如此驚訝。」
納蘭說罷,上香三炷。昭雪默默沉思:他竟也失去雙親,看這樣子,該是頭七。心中泛起一絲同情,默默走上前去,燃香三炷。
「呵。」納蘭輕笑一聲,道:「有你這位側福晉上香,他們泉下有知,亦該欣慰了。」
昭雪一驚,道:「甚麼側福晉?」
納蘭道:「你慌甚麼?出來講。」
說罷走出靈堂,昭雪亦跟出去。
納蘭道:「我已呈稟王上,納你為側福晉。」
「甚麼?」昭雪一驚,見他一身貴氣,側過臉,道:「你可有問過我?」
納蘭道:「你當日逼婚,可有問過我乎?」
昭雪面上一紅,道:「技不如人,你怎能生怨?」
納蘭忽而笑道:「如此說來,你便承認,還是吾之夫人了。」
昭雪道:「這便寫休書與你。」
說罷,提步回房,取來筆墨,寫將下來。
納蘭看罷,失聲而笑,道:「好吃懶做,無有擔當,便是吾之罪名麼?」
昭雪背過臉去,道:「休書已寫,你我再無瓜葛。我要走了,告辭。」說罷,起身取畫。
納蘭不急,緩道:「你能去哪裏呢?去找蕭姑娘,還是高雲天?」
昭雪聞之一驚,道:「甚麼蕭姑娘,我不便是麼?」
納蘭道:「難道這王府,還比不上落雁閣?還是,你又要心清氣正,不齒權勢名利了?」
昭雪心知他意思為何,便道:「若不是你拆了我的房子,我又豈會?」
納蘭道:「那我便賠給你間房子,你看這間,比之蓬門,如何?」
昭雪道:「差之千里。」
納蘭道:「你隨我來。」說著,便帶她來到一處大庭院:「這裏呢?」
「還是一樣。」昭雪道。
納蘭不服氣,一連換了三處別苑,才見昭雪眼中噙淚,道:「不必換了,沒有蕭姐姐,哪裏都是一樣。」
「你竟是為她。」納蘭方才醒悟,隨即笑道:「呵,我早該料到。然而,你可知她是何人?」
「是吾之救命恩人。」昭雪道。
納蘭嘆了口氣,道:「也好,你不知便罷。自古只有夫休妻,豈有妻休夫的道理。你好好休息吧。」
說罷,轉身欲行,卻又拋下半句話:「若是我得罪蕭姑娘,你必不樂意的罷?」
昭雪亦不示弱,道:「你又怎知,王上一定會准你呈請?」
「呵。」納蘭一笑,緩步而去。
芳月大婚
話說玉林酒醒,已是日上三竿,樹枝掩映之間,撒下陽光點點,叫人眼睛吃痛。
玉林坐起身來,只覺口渴難當,意欲起身伸個懶腰,卻發現自己竟被五花大綁,丟在一個老木樁旁邊。心下又驚又怒。回想昨日,自己被永延哈爾奇幾個人擁進廂房裏,便是一通灌醉,他一個人,哪裏招架得了這許多的觥籌交錯。實在撐不住了,只好借如廁之機跑到後院,只記得有一匹無頭怪馬,此後……便甚麼也不記得了,緣何自己會在這裏,還被五花大綁?正百思不得其解,突然,一陣冰涼水柱從天而降,砸得玉林跳將起來,抬眼一望,只見一個身著藍色紗裙的女子,正躺在樹上,悠閒地往下倒水。
「你是何人?為何拿水激我!」
「你可算醒了!」那女子手一揚,從樹上飛將下來。
玉林笑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落雁閣的蕭姑娘,怎麼這麼好興致,請本公子來這裏?」
玉林用盡全力,繩索卻絲毫不見鬆懈,反而越纏越緊。心裏暗想,這蕭姑娘打結的手法好生高明,並非善類,怎麼像個土匪?轉念之間,竟然哈哈大笑。
「你笑甚麼?」笑笑疑惑。
「哼,我笑你膽子忒小,心眼兒像芝麻,有本事放開我,咱們單打獨鬥!」玉林譏諷道。
「哼,就解開繩子,看你能如何?」
說著,飛刀過處,繩子登時散了一地。
玉林笑道:「就讓你見見玉林公子的本事。」說著,便是一躍,竟連片樹葉也沒搆著。心下好生奇怪,還以為自己酒飲得多了,傷身傷神,便靜心調息,運足功力,又是一躍,誰知還沒剛才高。心下頓時大駭,失語道:「怎會如此?」
鄭笑笑撿了個樂子,笑道:「玉林公子好高明的輕功,連棵樹也爬不上去。」
玉林頓時臉上佈滿紅暈,道:「定是這樹有古怪,否則我怎生爬不上去?」
「我看你是吃不到葡萄,倒說葡萄酸。」說罷,輕輕一躍,便到了樹梢,待往下看,卻是半個人影也無。
原來玉林故意激她,自己早一溜煙兒跑了。跑了一陣,向後一望,果然沒跟來,心下正慶幸,突然聽聞樹上有人輕笑道:
「飛不起來就用跑的麼?」
玉林一驚,轉頭欲奔,無奈慌不擇路,「光當」一聲撞在樹上,暈死過去。
笑笑從樹上跳下來,道:「還真是廢物一個。」說著,一把撂在背上,往樹林深處走去。
話說那晚,莫少飛看不慣他們流連煙花之地,離開之後,便來到了刑部侍郎嚴承義家中。
嚴承義正坐在院中小凳上劈柴,忽聽小童來報:「老爺,您那個忘年交、老朋友又來了……」
嚴承義起身,拭了拭頭上的汗珠,便聽到身後的人說:
「你可是當朝最窮的侍郎了!」
嚴承義不以為意,轉身笑道:「你倒是不請自進了。」
莫少飛道:「沒辦法,誰讓你家裏連買小廝的錢都沒有了呢?」
「哈。」嚴承義朗笑一聲,兩人坐於茶棚。
「瑾兒,去倒兩杯茶來。」嚴承義道。
瑾兒轉轉眼珠,卻然問道:「老爺是要兩年的陳茶,還是三年的陳茶?」
「呃……」嚴承義一時窘迫,道:「你看著辦吧。」
莫少飛咂了咂嘴,道:「看看,連小童都敢欺負你。」
嚴承義搖了搖頭,道:「沒辦法,瑾兒是我的廚師,老夫得罪不得。」
小童偷笑,道:「莫老爺難得來一次,就兩年的吧。」說著轉身去泡茶。
「瑾兒且慢。」莫少飛道。
「莫老爺甚麼吩咐,還是嫌棄我把你叫得老了?」小童道。
這話聽的莫少飛也是呵呵一樂,道:「你這小小年紀,叫我叔叔也是該的,去取兩個碗兒來,我自帶薄酒。」說著,從身後變出一潭酒來。
瑾兒見他竟自己帶了酒來,看來早料到自家寒酸,吐了吐舌頭,便跑掉了。嚴承義搖了搖頭,莫少飛一笑,打開酒封,一陣濃郁酒香飄滿小院。
「好酒!」嚴承義喜道,接過嘗了一口,道:「小子,果然了解老夫心意!」
莫少飛取了瑾兒拿來的兩個碗兒滿上,兩人連飲三碗。
嚴承義道:「這酒香醇,可不夠烈。」
莫少飛道:「我倒是覺得甘冽可口。兄長可是喜好更烈的?」
嚴承義道:「烈酒,最好是那種一飲便會醉的。」
莫少飛給他滿上,道:「下次,我便帶了更烈的來尋你,看你是否耐得住。」
嚴承義笑道:「哈,這世上還沒有我嚴承義吃不下的烈酒。」說著,又飲了一碗,道:「許久沒見你上朝,為何?」
莫少飛道:「老王爺暴斃,小王爺念仇心切,吾等不得擅離。」說罷,飲一口苦酒。
嚴承義嘆了口氣,道:「嚴芳已經回來了。」
「噢?」莫少飛詫異。
嚴承義道:「尚書大人親自接回來的。」
「如此兄長亦可安心了。」莫少飛道。
嚴承義又嘆了口氣,飲了口酒,苦澀難當,道:「小王爺如何了?」
莫少飛一擺手,道:「說好不論朝政只論酒,我剛才失了言,兄就此打住罷。」
嚴承義笑道:「呵,你這個年輕人,怎生個老頭子的倔脾氣。」
莫少飛道:「呵,天天陪你這個老頭子喝酒,還不是半個老頭子了麼?」
兩人邊笑邊飲,清風送情,把酒敘誼。◇
(待續)
-------------------
局勢持續演變
與您見證世界格局重塑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