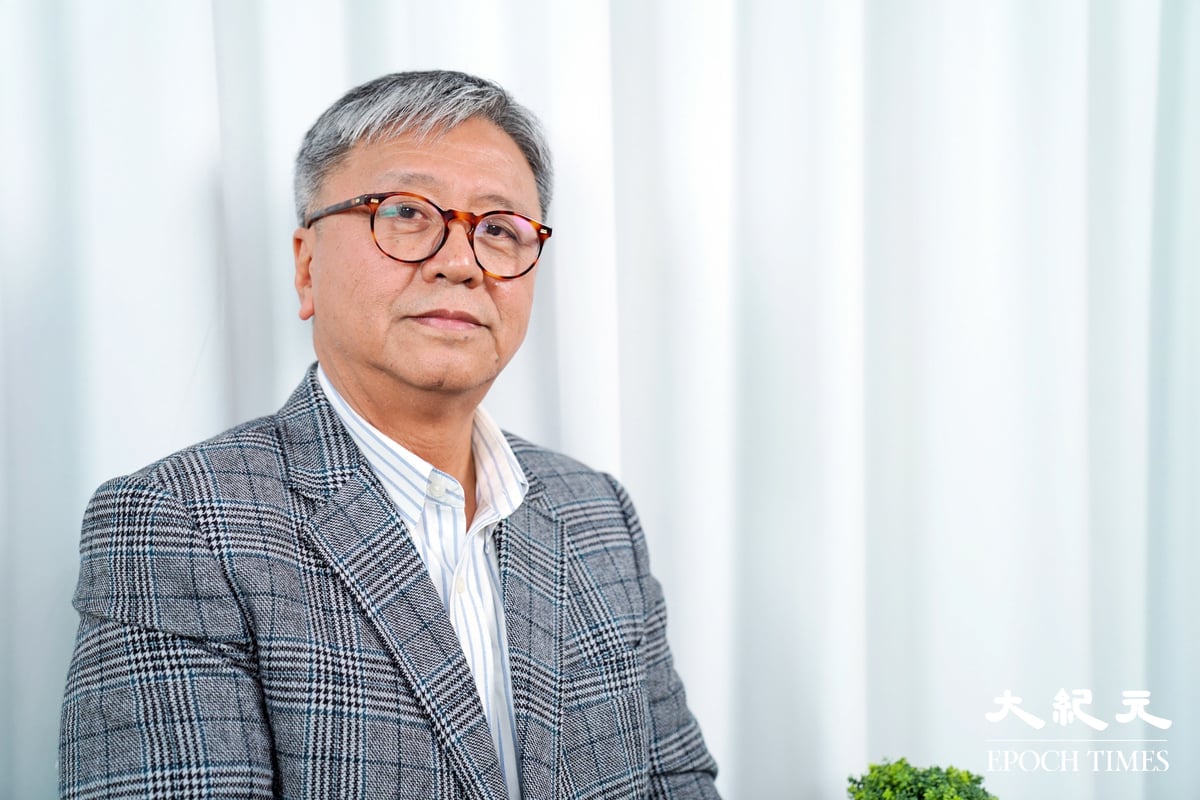「可以說我一生中有兩個最重要的變化,都是跟死亡有關係的。一個是1969年爸爸的死亡,讓我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從建築系改到哲學系。另一個就是2019年,香港的死亡,讓一個快到晚年,70歲退休的老翁,突然間逼我離開香港,變成一個自我流亡的知識人,這是我完全想像不到的⋯⋯」香港中文大學前哲學系主任張燦輝教授感嘆道。今期的「漂流傳奇」專訪張燦輝,與他談生論死,走進他鮮有公開的人生故事。
張燦輝出生在1949年,是「戰後嬰兒潮」的年代,那個年代的香港重光,從日軍的戰火中解脫出來,在英國統治下日漸恢復生機。他的媽媽在14年間生了10個孩子,可惜有兩個孩子夭折,他排行第三。年紀輕輕他就見證著自己的親人離世,「他們叫我三哥,二姐很早就去世了。」當時的他想不到,自己未來的工作的方向會跟生命教育息息相關,大半生都投身於中西方生死哲學的課題。
百廢待興時代 苦難與機遇交替
回憶童年,張燦輝自詡是「街童」一名,油麻地官涌街市就是他的成長空間。他憶述,當時他住在與六個家庭合住的公寓裏,沒有獨立的浴室和洗手間,要到街市附近的公眾浴室沐浴,基本的生活需求都要到公共場所解決。「我們個個都是窮的,不覺得有很大的問題,我們沒有特別的禮物,沒有特別的玩具,玩具是自己去創造的,自己去找回來的,都沒有人管我們的。到時間吃飯了,就回家吃飯,大部分時間都不在家裡,因為家裏的空間太小了。」
當時張燦輝的父親一個人挑起養家糊口的重任,是家中唯一的經濟支柱,「爸爸那時候在市區的一間茶居做事,他有份做股東,媽媽就是家庭主婦,每天在家做家務,照顧家庭。」父親對工作是百分之百的投入,他每天早上六點起床,忙到夜晚十一點才回家,十分辛勞。
「窮家人一磚腐乳就可以一餐飯,我們那時候去廖孖記買腐乳和豆腐花,甜的也可以,鹹的也行,是我們那個年代的記憶。」張燦輝描述,當時他住在街市樓上,街市旁有間紙紮舖,他打的第一份工就是在紙紮舖幫忙裝訂通勝,給自己賺一些零花錢。沒想到這個技能在多年後還能用得著,他到德國讀書時,需要影印很多資料,將這些材料裝訂成冊,靠的還是年少時期裝訂通勝學到的經驗。
在兄弟姊妹中,張燦輝是最擅長讀書的一個,他就讀伊利沙伯中學,後來考上港大,他並不認為自己有很高的天賦,與別人不同的就是他很勤力,而且與當時香港的社會環境有關:「當時的香港是自由、公開、開放的社會,尤其是在離開了大陸和臺灣的所有政治的紛爭之下,容許我們這樣自由發展,也造就了我們這一代最多的機會,不用靠家裏,不用靠背景,靠自己的努力是可以成功的。」他對比現在的年輕人,不由感到傷感:「其實現在他們就算讀完書,社會上有太多大學生、博士,就業機會和我們相比少了很多,面對的問題比我們當年多,我們當年是百廢待興的時代,很多東西可以做,只要你肯做、肯讀,就行了。」
「窮人孩子早當家」,隨後的日子裏,張燦輝很早就挑起重任,他半工半讀,在夜校當老師,並給學生補習,一個星期補兩三堂課,為自己賺取學費。他是家中唯一的一位大學生。談及六十年代從小就靠自己雙手賺錢的日子,張燦輝並不覺得非常辛苦,反而十分懷念當年只要勤力就能生存的時光:「在六、七十年代,只要肯去做兼職,在生活上都不是甚麼難事,那時候讀大學的人也不像現在那麼多。我覺得那時候香港有很多的機會,尤其是六十年代是充滿了發展的機會,慢慢就成為了一個特別的奇蹟,香港的奇蹟就是在香港人奮鬥之下,建立起來的成就。」
追問生命的不確定 投身哲學行列
1969年,張燦輝經歷了青年時期最大的一次創傷,若說童年時還不太懂得死亡是甚麼,這一次是切身體會到死亡是那麼近。那時他剛剛考上香港大學建築系,家中就傳來父親被小巴撞死的噩耗,竟然是在一條不准駛入的路被撞倒,拋下妻兒撒手人寰。
這一切來得太突然,父親是家中的頂樑柱,還有好幾個正在讀書的兄弟姊妹,母親又是全職的家庭主婦,命運到底在開甚麼玩笑,讓父親就這樣毫無交代地離開。青年時代的張燦輝,內心充滿了對人生的疑問,追問著生命的意義和存在的不確定性,渴望對生命有所解讀,哲學就成了他當時最嚮往的議題。於是他毅然決然選擇轉系,來到了香港中文大學讀哲學。這一投入,就是人生四分之三的日子,從學生到教授,他的生命都浸濡其中。
中大哲學系的創辦初期,有多位大名鼎鼎的哲學家作為奠基人,都是從大陸逃至香港的文人,錢穆、唐君毅、牟宗三,這批真正熱愛中華文化、有骨氣的文化人,反對中共馬列唯物主義,在香港這片自由的土壤中傳播儒家思想,新亞書院由此起步,成為大陸流亡學者重新反省亞洲文化及中國文化的唯一地方。隨後勞思光加入崇基書院,成為張燦輝生命中的恩師。這些赫赫有名的哲學家,保留著中國傳統文化人的禮儀和風範,啟發了他的世界觀。
他回憶:「那時候我們和老師的關係是非常親密的,我差不多到過所有老師家吃飯,老師跟我們的關係非常好,同時給我們絕對的自由度去發展自己,與老師不同意見時我們可以發表評論,也都接受我們的意見。那時候,真是我一生中開心的、最浪漫的、最好的時代!」他又一針見血指出,只有當年的師生關係才有那麼親密,如今的師生是互相防備,老師說的話會被舉報,學生有自由思想也可能遭遇危險,人與人之間已不是正常的關係了。他感恩,自己所在的年代遇到的老師並非只是一個傳授知識的工具,他們從人性化、充滿人文關懷的的角度來影響學生,也造就了一批帶有自由思想、不畏強權的真香港人。
一提到中大,就觸及到張燦輝的敏感神經:「可以說,我從1970年入讀中文大學,除了中間有幾年到德國讀書,有幾年去了浸會之外,我一輩子都在中文大學,叫我怎麼不懷念!那時候,崇基學院的山上只有甚麼呢?兩個水塔,在過去幾十年中,我看到中文大學一步一步的改變,建築一棟棟起來,這裏是我人生中我生活的地方,怎麼可以不懷念呢?」
見證「香港之死」 70歲流亡海外
張燦輝原以為自己可以在充滿理想的中大終老,在退休日將近時,沒想到中大變色,香港變色,此時此刻,張燦輝描述自己見證著「香港死亡」,這是他研究死亡議題一輩子,在古稀之年要面對人生又一個痛心的選擇。
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中大變成了戰場,按照張教授的話說就是「山城變色」,中共的黑手伸入校園,動搖了學校最可貴的精神,由反共文人一手一腳建立起的民主根基和自由學術思想。甚至在2021年,當自由民主女神像被人半夜三更搬走的時候,也沒有老師發聲。
「回不去的中文大學」和「回不去的香港」,是張燦輝這幾年來常常掛在嘴邊的話,並著書《山城滄桑——回不去的中文大學》表達自己心中的悲憤。他形容自己是「自我流亡的知識人」,2020年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離開香港,到英國「避秦」。他認為香港山河已變色,無論是留在香港還是離開,其實都處於一種「流亡」的狀態。
在2022年出版《我城存歿》時,張燦輝提到,「香港」(Hong Kong)成為歷史名詞,如今應該稱香港的普通話發音「Xianggang」,失去了自由民主的香港將淪為大陸的一個沿海城市。他在再版的前言中寫道:「Xianggang現在是:謊言即真理/強權即民主/服從即自由/人治即法治/馬照跑,舞照跳,吃喝玩樂即太平盛世。」
去年和今年,他被台灣清華大學和多個大學、機構的邀請,擔任客座教授。「在台灣的生活我非常開心,台灣也有我的學術圈,還有我的朋友,這裏還是一個自由之地,我可以說話,除了學術課題外,我也想講一下在我的生命裏面,怎樣理解當前世界的文化和我們面臨的情況。」
今年適逢「雨傘運動」十周年紀念,張燦輝亦出版最新作品《傘後拾年:夏慤村的未圓夢》,收錄了79張他在2014年「雨傘運動」佔領區現場拍攝的黑白相片,以夏慤村的「烏托邦」為主軸,著重表達這79天「愛與和平的世界」,也將在9月14日至30日在台北舉行攝影展,並透過講座等多種形式的交流活動,可以海外更多的朋友認識到香港發生的事,以及理解他「出走」的因由。
如今已75歲高齡的張燦輝,仍然退而不休,忙碌籌備著講座和展覽。在中秋節前夕,當他得知屹立香港23年的《大紀元時報》將在當地暫停印刷業務,於8月17日出版最後一期實體報紙,轉為網站運作時,他感到悲憤交加。他寫下感言:「在2024年的香港,還有什麼實體報紙可買可看?《國安法》的降臨使新聞和言論自由沒有了,白色恐怖籠罩着整個社會。香港大紀元時報在這艱難時刻仍然維持到今天,已算是奇蹟。但最後都要結業,見證香港最後一點新聞自由也被取消,能不悲哀憤怒嗎?」他又鼓勵大家不要放棄:「不過,離開專制獨裁的共產黨地方,回到自由開放的世界,繼續發揮獨立傳媒的任務,也是值得大家肯定和支持的!不要放棄,捍衛自由!」◇
------------------
🗞️9.17暫別實體 立即預購
https://bit.ly/buybyepaper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