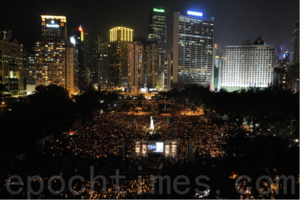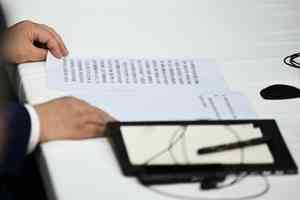觀塘裁判法院今早聆訊一宗「虐兒」案,被告是42歲的蔣定邦。據《東方日報》說,蔣在英文控罪書上報稱是警察,中文控罪書上則報稱是「其他職業」。
蔣定邦被控一項「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控方指他在 2018 年 12月1日至 2019年2月19日,在油塘油翠苑漾美閣一單位,故意襲擊、虐待或忽略九個月大的蔣天晴,做法很可能導致蔣天晴受到不必要的苦楚或健康損害。該男嬰已因本案夭折。
據《法庭線》報道,裁判官溫紹明問:「小朋友因為呢單案過身,會告嚴重啲嘅罪?」控方回答:「攞咗法律意見會告呢條。」溫再問:「死因係咩?」控方指「呢個好難解決,決定咗告呢條」,溫官聞言稱「嘩」。(注1)
蔣定邦選擇自辯(不知道自辯理由是否「浪子回頭金不換」),溫紹明提醒他案情嚴重,應該聘請律師,案件押後至8 月7日再訊。
裁判官那一聲「嘩」,不禁引發了我的好奇心。這個「嘩」字通常表示驚訝,而能夠令溫紹明驚訝的東西,不外乎以下三點:
一、嬰兒死了,涉及一條人命,控方只告父親「虐兒」,罪名未免太輕;
二、案發至今五年,警方依然查不清嬰兒死因;
三、確定不了死因,便「決定」只告罪名較輕的虐兒了事。
嬰兒死因有什麼「難解決」呢?查一查2019年的媒體報道,原來當年2月19日凌晨4時許,警方接報抵達現場,發現男嬰昏迷不醒,送院後證實不治。警方初步調查,懷疑男嬰睡覺時嘔奶窒息致死,但後來取得一段閉路電視片段,顯示男嬰死前有人涉嫌疏忽照顧,於是拘捕了蔣定邦。
看五年前的新聞,大家也許覺得男嬰之死只涉嘔奶窒息,極其量是蔣定邦當晚疏忽所致。但再看一次今天的控罪,卻是「在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2月19日⋯⋯故意襲擊、虐待或忽略九個月大的蔣天晴」。不是一晚的疏忽,而是接近三個月的「故意襲擊、虐待或忽略」。
以上日期很耐人尋味。男嬰九個月大,但他出生後的頭六個月,蔣定邦似乎仍是個慈父。為什麼2018年12月1日一覺醒來就「鬼上身」呢,抑或發生了一些家庭糾紛,令他性情大變要向男嬰施虐?若是後者,就顯然不是「虐兒」那麼簡單,也難怪裁判官要「嘩」。
查香港《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7條(即被告的控罪),本案若循「公訴程序」起訴,一經定罪,可處監禁10年;若循「簡易程序」提告,則刑罰較輕,頂多監禁3年。此案由觀塘裁判法院處理,而裁判法院就單一控罪的最高判刑只是兩年監禁,可知控方不單「決定」了一條特別輕盈的罪,似乎更「決定」以最溫柔的方式提告。
蔣定邦決定自辯,可能也看通了這一點,才坐定粒六,覺得連律師費也可省掉。不禁想起日前另一判決:一個女警長涉於2019年在會所偷取兩支USB及28張總值2,400元的書券,去年被裁定盜竊罪成,判囚8個月,女警長決定上訴。
本月18日,暫委法官郭啟安頒下判詞,認為上訴人作為資深警員,明知案發現場設有閉路電視,不可能冒失去工作及長俸的風險,作出必被揭發的偷竊行為,未能排除她誤將書券帶回家,及誤以為USB是可取走的紀念品,於是裁定她上訴得直,撤銷定罪及判刑。這樣的判案邏輯,我也忍不住「嘩」了一聲。
當然,你可說這是「合理懷疑」讓警員脫罪,只是我不知道同類懷疑是否在任何人身上也同樣「合理」。蔣定邦此案不是也有閉路電視片段作證嗎?如果蔣明知有閉路電視,他應該也「不可能冒失去工作及長俸的風險,作出必被揭發的虐兒行為」吧。
此案審下去,不知還會引發幾多個「嘩」?洗耳恭聽。
注1: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自「馮睎乾十三維度」Patreon
(編者按: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
-------------------
局勢持續演變
與您見證世界格局重塑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