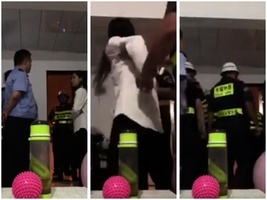「我的父親又被非法綁架了。我幾經要求,見到父親時,他被關在鐵欄後,頭髮斑駁不堪,衣衫襤褸。從父親斷斷續續的訴說中,我知道他一定是在鬼門關走了一遭。」吳駿逸說。
一段痛苦的過往或許可以選擇將其塵封,但不經意提起時,卻仍是那樣的刻骨銘心。
「在我母親被捕半年後,我們終於見到了她。我在路上反覆想像見面時的情景,但當母親進來時,我竟完全不認識了:眼前這個人骨瘦如柴,蓬頭垢面,鎖骨和臉上的顴骨瘦得尤其突出,眼睛往外凸,整個人看起來就像立著的一副骨架。我被嚇得一下晃了神,定睛再看,這是我的母親啊!我當下不由自主地就跪在她面前大哭起來。」
來自中國湖南80後的吳駿逸,繼續講述她一家人過去二十多年的遭遇。
「我的父親又被非法綁架了。我幾次去市公安局要求探視,當我見到父親時,他被關在鐵欄後,頭髮被剃得斑駁不堪,衣衫襤褸。從父親斷斷續續的訴說中,我知道他一定是在鬼門關走了一遭。」
「當時我才十幾歲。」吳駿逸說。
雖然事過境遷二十餘載,但她清晰記得:「當時我心裏難過得揪心揪肺,只能放聲大哭,我想既然甚麼都做不了只能哭,那就哭得大聲一點,讓大家聽到也來見證這是個甚麼世道,為甚麼好人要遭受這樣的苦難?」
兩年美好時光
7月8日,吳駿逸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回憶說,她的青春只度過了兩年美好的時光。
「我們家是中國常見的3口之家,父母在國企工作多年,家裏算是比較寬裕的。」只不過父母的婚姻沒有感情基礎,生活的背景又截然不同,她說:「如果說他們兩人完全相反也不盡然:他們的性格之前都是一樣的固執和自我。」
這就導致了父母婚後爭吵不斷,兩人甚至決定等孩子大一點時就離婚。
吳駿逸這樣形容父母當時的感情:「我父母雖然在同事朋友眼中還是好相處的人,但一回到家裏,他們就變得互不相讓,矛盾不斷。母親敏感好強,父親木訥寡言,再加上他們都很倔強,因此在我的印象中,吵架是家常便飯,打架我也見過幾次。我10歲左右時,父母就開始商議離婚。」
由於婚姻不幸福導致長年心情鬱悶,吳駿逸的母親本就不好的身體,更是亮起紅燈,多種疾病纏身。直到1997年,父母開始修煉法輪大法,這一切都奇蹟般地發生了改變。
「修煉一個多月後,父母的爭吵就很少了,母親的身體似乎也越來越好,父親的話也多了起來。剛開始我雖然不太清楚是甚麼改變了他們,只覺得家裏經常充滿了歡聲笑語,精神和物質條件都越來越好。」她說。
「慢慢的,父母會到公園和同修家一起學法、煉功,那帶給我的回憶都是非常祥和、美好的。」說話間,她勾勒出一幅美好場景,「記憶中,大人在清晨的陽光下打坐,悠揚的音樂讓人心情舒暢,我們幾個小孩在一邊有時跟著一起煉,有時在一起玩鬧,大家就像親人一樣,每個人都笑容可掬、和藹可親。」
從此,「真、善、忍」也在吳駿逸的心中紮下了根。
被毀掉的青春
1999年7月20日,中共開始全面迫害法輪功。鋪天蓋地的打壓,也將吳駿逸推入災難的深淵:「我父母因不願放棄修煉,遭受了中共的非人折磨。迫害開始後,我們家一直處於破碎、離散的狀態。」
她的父母不僅被剝奪工作,因不放棄信仰,還多次被非法綁架、被迫流離失所,甚至遭到非法判刑。
吳駿逸說,那時的她非常害怕和恐慌,神經始終處於緊繃狀態。
15歲被關在警局的那個寒夜
2001年3月的一天,吳駿逸正在學校教室上晚自習,突然被叫到校長辦公室,裏面坐著好幾個自稱是公安局的人,他們試圖打聽她母親的去向。
「母親那時早已被公司開除,被迫流離失所,有家不能回,所以具體住在哪裏我也不知道。為了彼此的安全,母親只是偶爾聯絡我,然後偷偷見一面,每次見面的地方也不一樣。」在父母反覆被綁架後,吳駿逸不得不小心翼翼回應陌生人的問題。
盤問了大半個小時後,警察見套不出話來,就將她強行從學校帶回公安分局逼問。
她回憶道,「半路上,一位女警欺騙我說,告訴阿姨你媽媽在哪,我們保證不抓她,因為這算自首,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不然就要判重刑!」由於當時年紀小,吳駿逸信以為真,便透露了她與母親見面的地方。
「到了警局,幾個警察到辦公室跟我『聊天』,他們從開始的偽善,慢慢變得越來越急躁、凶狠,估計是沒有在我透露的地點抓到任何人。而我也明白了他們是騙我的。」直到凌晨3時左右,警察陸續離開,卻將15歲的吳駿逸鎖在辦公室裏,一直關到第二天下午。
「警察還警告我不准告訴親朋好友。老家的3月春寒料峭,我從教室出來時本以為只是出去一會兒,外套也沒穿,夜裏冷得只能跳來跳去保持體溫。」她說,「這一晚真是飢寒交迫,我望著鐵窗外,明明是很熟悉的街道,卻感到分外陌生,壓抑又恐怖。」
那一晚,她也忽然想明白了很多事:「我從未想過迫害可以離自己那麼近,我也沒想到為甚麼周圍警察的面色會變得如此可怕,根本不是我童年起所接受的教育中描述的那樣美好,甚至比我那個年紀認為的壞人還要壞。但與其說害怕,不如說我認清了中共制度下的所謂公安人員的真面目。」
父母遭酷刑折磨
後來,吳駿逸的母親還是被綁架了。2001年6月至2002年1月,母親被關在衡東縣看守所,家人無法探視。
「父親只能不停出入我們當地的公安局,要求見我母親。」大約半年時間,吳駿逸終於等到會見母親的機會。
在小房間等待時,她突然聽到走廊傳來一聲聲『咣當、咣當』的手銬腳鐐碰撞的聲音,「當人走近時,我看到的是一副『人體骨架』。我母親原本的體態是比較偏胖的。我當下不由自主地就跪在母親面前大哭起來,叫著『媽媽,媽媽,您怎麼變成這樣?』她想安慰我,但卻發不出任何聲音。母親當時體重從55公斤驟減至25公斤。」
說到此,她不禁流下眼淚:「那對我衝擊非常的大。即使已經過去這麼多年,很細節的部份可能我都記不得了,但每次說的時候我都能清晰感受到當時的驚怵。」
後來吳駿逸還得知,看守所的獄警變著花樣摧殘母親,試圖逼迫母親放棄信仰:用一根一米多長的粗鋼棍,將母親的兩條腿分開成一字型銬在兩頭,使腳不能彎曲,睡覺也不能翻身;用掃帚劈頭蓋臉地打母親;吃的飯,是漂著幾片有蟲卵爛菜葉的鹽水湯,和落滿一層蒼蠅糞便的黑米飯。
過後不久的一個周末,當吳駿逸從學校回到家後,發現家裏被翻得亂七八糟:心想父親又被捕了。「據父親後來告訴我,他當時被警察從7樓一路往下拖到樓下的車裏。到了衡陽市公安局,警察用手銬把他吊起來毒打,折磨得奄奄一息後又被立即轉入了衡陽市第一看守所,並交待那裏的獄警把父親放進最惡毒的監室。」
最惡毒的監室意味著甚麼?她說:「父親一進房間就遭到群毆毒打,打得他頭破血流昏死過去,被搶救過來後,獄警又把他放回同一個監室繼續折磨。」
小小年紀的她被警察勒索幾百元後,才終於在警察的監視下見到了父親,「我父親被關在鐵籠子裏,我只能站在鐵籠外與他對話。我不明白,我母親和父親都是那麼好的人,為甚麼要被關、被打?」
再次回憶這些事,吳駿逸幾度哽咽。「所幸我父母現在的身體在繼續煉功後都恢復了健康。」但她心中仍非常心疼二老當時的遭遇。
接到父母的判決書
吳駿逸從12歲就開始住校,「以往周末回家,父母都會準備好吃的等我;但迫害後,我從學校回到家,才明白我們的家已經沒了,打開門見不到父母了。」
那年還在讀高中的她突然接到父母「判決書」的那一刻,一種窒息感瞬間將她淹沒:「我先是接到父親被判勞教兩年的通知,緊接著,又收到一張我母親被判4年的判決書。」
「當時我全身發軟,腦袋裏一片空白。到了晚上,我癱倒在床上,腦子裏不斷重複著:我的父母都在監獄,他們怎麼辦,我怎麼辦?」
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她都覺得做任何事情都沒有意義了,雖然還是按部就班地上學,但好像只是麻木地維持著日常生活,對未來不抱任何希望和憧憬。
拖兩個箱子長途探視雙親
吳駿逸記不得自己為此哭過多少次,但「好人沒錯、父母無罪」的信念一次次支撐著她:她不間斷地打電話到監獄,要求履行探望父母的權利。
「父母都被關在長沙,去那裏需要先坐火車,再轉兩趟車去看母親,然後又轉兩趟車去見父親。」她說,最初要求探望時,母親所在的監獄三番五次推脫,「等了好幾個月後突然說可以接見,我高興得趕緊給父母準備冬衣、日常用品和一些食物」。
從衡陽市通往長沙的綠皮火車是凌晨3時出發,第一次趕火車的她拖著兩個大箱子一路奔波,終於上了車,發現連座位都沒有,只能坐在箱子上。
「夏天的長沙就像蒸籠一樣,熱得頭皮都發脹。到了長沙女子監獄門口,我已經精疲力盡,但監獄門還沒開。我累得席地而坐等了一個多小時,心裏一直期待著很快就可以見到一年多未見的母親了。」
沒想到監獄傳達室的人忽然出來說:「你回去吧,你媽在裏面表現不好,不讓見!」
「我瞬間就傻眼了,哀聲求他們讓我與母親見一面,監獄的人卻喝斥我趕快離開。當時我站在扭著鐵絲網的高牆邊上,無助和難過一下子湧了上來,我只能蹲在地上哭。」吳駿逸辛酸的回憶著。
哭完了,她再次整理一下情緒,趕車到另一個監獄探望父親,「不然錯過時間連父親也看不到了」。吳駿逸說,「回到家通常已經是第二天凌晨了,休息後簡單收拾一下還得趕回學校。」
在父母被非法關押在監獄的時間裏,她都是這樣的兩地奔波來去探監。◇(下篇將在本星期五於B8版面刊載)
------------------
⏪️ 回顧2024專題報道👇🏻
https://hk.epochtimes.com/tag/回顧2024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