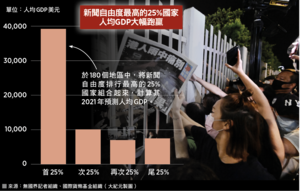閱讀前文:【專訪顏純鈎】回望香港 讓我感恩讓我悲
顏純鈎曾任職於香港數家紙媒,後任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他出版的作品包括了小說集、散文集、劇本等,獲得過香港第八屆青年文學獎小說高級組冠軍、博益小說創作比賽冠軍及台灣行政院新聞局電影劇本徵選優異獎。主要作品有《紅綠燈》、《自得集》、《血雨華年》。《香港我的愛與痛》是顏先生2023年底出版的新作。
在大陸三十年:活在階級鬥爭中 文學創作只是夢
1. 對文學的熱愛始於閱讀
顏純鈎介紹:「我自小有機會讀很多書。我媽媽以前在鄉下的醫院工作,那個醫院是個華僑建的醫院,那個華僑很有心,他在醫院專門建了一個圖書館,想讓病人留醫時都可以看書。醫生、護士都可以看書。圖書館專門請了一個人去管理,管理員購進了很多世界名著。因為我媽媽是職工,所以我們那時在圖書館借了很多書來看,起碼有一兩百本世界名著,文學閱讀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我讀的中學在福建的南部,叫養正中學,也算是福建的名校。學校那個圖書館有上百年歷史,藏書很豐富。文革前我們閱讀基本上是自由的,雖然文革開始時有些政治理論要讀,但圖書館裏的書就沒有限制,所以我們那時看了很多書,這為日後寫作打下了一個基礎。」
2. 「借書」的故事
文革期間,除了毛選(《毛澤東選集》)和一些政治理論文章、革命書籍,其它各類圖書基本屬於「四舊」、「封、資、修毒草」,被大量封存、銷毀。顏純鈎提到了他在圖書匱乏年代的一個「借書」的故事。
顏純鈎回憶道:「那時有一段時間,我因文革武鬥受傷,住到在學校工作的姑姑、姑丈家休養。那間學校有一個圖書館,就在我住的同一層樓、我房間的隔壁,文革時圖書館就被封起來了。後來因為窗戶玻璃都破了,就用木板封起來。我每次經過時,總覺得這麼多書不能看太可惜了。有一天我手發癢,就去摸一下,發現原來有一個木條鬆了。於是,到夜深人靜時,我就拿著手電筒進去翻書。每次都捧著一堆書出來,回到自己的宿舍去看,看完又「還」回去,然後又再「借」一批出來。
3. 關在抽屜裏的文學夢
從小喜歡文學的顏純鈎,在大陸文革時期也曾寫過一些文章。顏純鈎表示:那些文章「根本沒有機會發表,自己寫完就放在抽屜裏。因為在大陸要發表作品要查你三代、查你的政治背景、你的社會關係、你在單位的政治表現。我知道我是沒甚麼機會的,所以基本沒去投稿。」
後來,顏純鈎認為,在大陸時思想是受到束縛的,所見所聞跟後來在香港看到的完全是兩回事,所以覺得那些文稿已沒有價值,就處理掉了。
4. 閱讀帶來了反思與轉變
「以前我們都崇拜毛澤東,但是到了文革後期,我們已經開始對毛澤東產生了懷疑。因為文革初期,你說紅衛兵是革命小將;到文革後期,你說我們是黑五類、黑九類,要接受再教育。究竟我們是你的寶還是你的垃圾呢?文革後期我們看到了很多政治思想的書,整個人的認識、思維開始發生改變。」顏純鈎談了他文革後期思想的轉變。
在香港四十年:脫胎換骨 超越夢想
在《香港我的愛與痛》中,顏純鈎提到:「我從小喜歡文學,文革中又參與政治,對思想文化方面興趣頗濃。」不過,他能夠有機會廣泛涉獵各種書刊資料,能夠一生從事自己喜歡的編輯工作,能夠自由地寫作、發表文章、出書,不但樂在其中,而且還超越了他對自己的期望,這一切,卻是在香港實現的。所以,他會有「沒有香港,便沒有我的一生」的感慨。
1. 理想是前進的動力
「那時在香港做報紙人工很低,我剛入報館做校對只有600元,我的同學在工廠做,他們如果加班,基本上有1200-1300元,是我人工的一倍,我媽媽有一段時間叫我不如去做工廠。我跟她說,如果做工廠我就不來香港了。」
顏純鈎繼續追尋他的文學夢。
「因為在報館上班,中間有很多空檔時間,工作到差不多,手頭沒工作我就看很多報紙。那時看很多台灣報紙、香港報紙副刊。半夜下班,第二日早上十點起床,一直到整個下午都無事做,我就可以去圖書館借書回來看。做校對的那段時間,其實就是我自己進修的時間。」顏純鈎沒有進過香港的學校,憑著對文學的熱愛和勤奮與天賦,自學成才。
2. 堅持寫作 即使退稿裝滿了紙箱
顏純鈎的正業是編輯。他表示:「其實創作都是業餘,是自己有興趣。」
他還記得,初到香港時文化環境還很好,很多報紙都辦副刊,刊登了很多純粹的文學作品。他強調:「有很多文學雜誌,是純粹給你寫文學作品,不是寫普通的雜文、散文,你是可以寫小說的。那時我有空就寫,寫完就去投稿。不過,投稿後不斷被人退稿,退到裝滿我床底下的整個紙箱,我媽媽說為甚麼就見你寫,不見發表?」
3. 從思想上脫胎換骨 迎來新生
顏純鈎認為,香港的生活對他的創作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在香港,首先受到的影響其實是人格上的,就是你對社會的看法,你對人生的看法,你對歷史的看法,很多都是屬於人生觀和價值觀,那部份其實我是等於一種新生,就是舊的東西全部丟掉,新的東西生出來。」
他記得:「在香港有記者訪問過我,我說有一套越劇叫《追魚》,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追魚》就是一個鯉魚仙女,去到凡間就喜歡了一個書生,兩個人相愛就成親。誰知海龍王不讓她結婚,要將鯉魚抓回去。鯉魚就將自己身上的鱗片拔下來還給父親海龍王,就是欠你的東西我歸還給你了。我的脫胎骨其實差不多是這樣,那個過程是很痛苦的,但有那麼多時間讓我改造自己,我覺得改造完也真的有新生的感覺。」
當共產流毒被清除乾淨後,顏純鈎的創作獲得了突破,開始得到了高度評價。
香港不是文化沙漠
曾幾何時,香港被人說成是「文化沙漠」。顏純鈎認為,那是香港人自嘲多一些。大陸反而是,經歷文革那麼多年,「那裏才是文化沙漠,香港不是」。
「台灣的戒嚴時期,那的文化開放都不如香港,人們接觸到現代文學的一些理論、作品,其實很多都是香港過去的,因為台灣當局那時不讓民眾接觸,尤其不讓接觸大陸五四時代的東西,所以台灣那時的文學雖然出了一些作家,但整個社會其實都是比較沙漠化,不如香港那麼好。
「香港反而是最自由的,最令有志於文學的人可以自我發揮的地方。問題是香港本身是一個商業社會,一般文人在這個社會地位不是很高,所以,好像在香港你是文人沒甚麼出色,其實不是的。看社會文化水準,同樣擺在70年代來比較,香港人不會比大陸人差,不會比台灣人差。」
對於香港作家繼續創作的思考
1. 本土創作不能觸碰敏感內容 思想深度會受影響
環顧今日香港,隨著《港區國安法》和23條的實施,言論自由在香港應該說已經結束。《蘋果日報》、眾新聞、香港電台一一被消失,見證過香港文化的黃金歲月,顏純鈎對與香港本土還有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創作,是怎麼看的呢?
顏純鈎認為:「應該都會有些人會堅持。一個地方的文化從很繁榮,一路沒落下去,都是有個過程的,所以說現在香港變到完全沒人寫作了,那倒不會。你探討人性的東西,探討一些文化、思想的東西,你不接觸敏感政治都還可以的。等於以前你在大陸,雖然政治禁錮那麼多,但說幾十年間完全無精品那倒不會。
「創作靈感可能一路都會有,但思想性就會差些。因為你沒有自由去想問題,你想到這些不行就止步,想到那些不行就又止步,創作的空間在政治邊界內,然後你在這個圈內去想問題,你的思想深度就會差些。」
2. 離開那塊土地 感覺慢慢會有間隙
這幾年,很多香港作家不得已離開了香港。顏純鈎覺得:「出來了的危險是,因為你離開了那塊土地,感覺就不會那麼強烈;而且你不是跟那個地方的人一起生活,你對生活的觀察就會有些隔膜。如果來了溫哥華十幾廿年,你反映加拿大華僑圈子的生活可能就行,但你說我還是寫回香港,這已經是與香港有間隙的了。」
3. 變換角度繼續寫香港
顏純鈎表示:「其實現在我都逐漸發現,因為時間長了,時事的東西有時候會重覆的。比如你講共產黨,共產黨這麼多東西講到都差不多了,它有新的東西我們會再挖一些新的感受出來,但慢慢都會覺得那些理念方面是會有些重覆的,你老是寫重覆的東西就自己都覺得沒有意思。將來或者我有機會寫一些我以前在香港生活、一些文化界的一些活動,或者一些當時的一些社會面貌,一些比較自己有感覺的人。那些不一定是作為時事來看,會作為一種人生的記錄。」他覺得,雖然快餐文學在當今社會會得到了更多的關注,但是純文學才有永恆的價值。
《香港我的愛與痛》是寫時評的意外收穫
《香港我的愛與痛》主要是反送中以來,顏純鈎在Facebook發表文章和少量蘋果社論的結集。其實,顏純鈎寫時評歷史悠久。他從70年代剛到香港時就開始寫一些政治評論給李怡主編的《七十年代》發表。大概寫了一年,後來興趣轉到了文學。
直到「佔中」,機緣巧合下,開始「重操舊業」。
「那時戴耀廷、陳健民他們幾個宣傳『佔中』(佔領中環),我有一日在《信報》看到戴耀廷的評論,他提到一個概念叫做「違法達義」——違反法律,達到道義。這個概念對我有很大衝擊,因為在我們的認識中,違法是不行的。原來比法律更高的是道義。
「他們要佔中時,我是覺得有點懷疑的,你把中環的路佔了,人家不用上班、不用做生意?這樣做對不對?但他這個概念打動了我,我就寫了篇文給《蘋果日報》,講我對這個概念的一些認識。《蘋果日報》發表了,然後我就開始再寫。
「那時因為我還未退休,公司有些左派背景,我不想給公司帶來尷尬,說你個總編輯在這裏寫些這樣的東西,我老闆見到中聯辦的人很難交代,我就用筆名去寫,一直寫到我退休。
「退休之後我就轉去寫文革長篇,就是中文大學出版的那個文革長篇《血雨華年》。這樣又停了,一直到回來溫哥華,接著就是『反送中』,然後我就開始再寫。」
在《香港我的愛與痛》一書中,顏純鈎主要是想分享他對一些政治、時事的看法。因為在他的人生中幸運接觸到很多品質很好的、有影響的前輩,所以,書的最後的部份,他想跟讀者分享上一代是怎樣處事、待人,「希望大家都多少可以學一些」。#
-------------------
局勢持續演變
與您見證世界格局重塑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