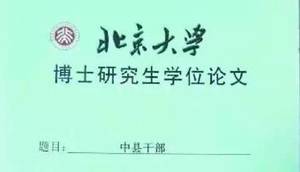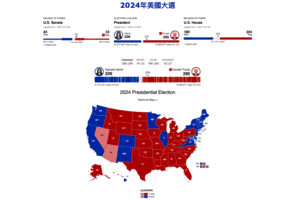1966年6月10日,北京大學最年輕的文科教授之一,被當代中國著名學術大師陳寅恪嘆賞為「思路周詳,文理縝密」,「誠足當所謂好學深思者」的汪籛教授,在家中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身亡,時年50歲。
文革狂風吹進北大校園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得到當時的中共獨裁者毛澤東的支持,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中共掀起一股新的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否定中華五千年傳統文化的浪潮。一些還保留了一點點傳統治學理念的歷史學家,成為被猛烈攻擊的對象。
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發。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人貼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甚麼?》的大字報。6月1日,根據毛澤東的批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播報這張大字報。
當晚,中共華北局派駐北京大學工作組進校。6月4日,新北京市委負責人到北大宣佈:撤銷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珮雲的一切職務,由工作組代行黨委職權。工作組指責原北大領導為「反革命黑幫」,號召學生「揭發」、「鬥爭」原來的校領導和一些系領導。
汪籛當時是北大歷史系副主任,也成為重點批判對象。歷史系的學生把批判他的大字報貼到他家的門上。大字報脫落在地,並且破碎了。有人說,汪籛看到大字報非常生氣,把大字報撕下來了。
汪籛的學生批判他撕毀大字報,是對抗和破壞文革。汪籛不承認他撕了大字報。當時執掌北大的「工作組」責令臥病在床的汪籛,照原樣把大字報修補好,並重新貼好。汪籛作了工作組要他做的事後,把自己反鎖在房間裏,服下大劑量「敵敵畏」。
汪籛曾是陳寅恪的得意門生
汪籛,1916年生於江蘇揚州。1934年秋,考進清華大學歷史系。在當年清華大學300多名新生中,他的入學成績總分名列第二,且數學獨得滿分100分。1939夏,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做研究生,導師為陳寅恪教授,地點在昆明西南聯大。
1947年6月,他輾轉來到北平,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繼續完成他的研究生畢業論文。期間,主要在清華大學協助他的雙目失明的老師陳寅恪寫《元白詩箋證稿》,有將近一年的時間,吃住都在陳寅恪家。
陳寅恪的學問有多高?歷史學家傅斯年的評價是:「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陳先生又是怎麼評價汪籛的呢?
1948年5月17日,陳寅恪在致北大歷史學家鄭天挺的信中寫道:「汪君自借住弟處以來,於今行將一載,弟深知其深宵攻讀,終日孜孜,而察其史料之熟,創見之多,亦可推見其數年來未嘗稍懈,誠足當所謂好學深思者。」
能得到陳寅恪如此高的評價的人,那就不是一般的才子了,而是將來可以成大家、擔大任的棟樑之才了。
汪籛被陳寅恪逐出師門
1949年10月1日中共奪取政權後,便開始對知識份子進行系統的思想改造。汪籛受時代大潮挾裹,跟當時的許多青年知識份子一樣,對中共寄予希望。1950年2月,汪籛加入中共;1951年冬到1953年底,在馬列學院二部學習了兩年,由一個傳統的歷史學者,逐漸轉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者。
1953年,中共中央所屬的歷史研究委員會決定,由陳寅恪出任中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為了讓在廣州任教的陳寅恪北上,有關方面先後派遣陳寅恪的老友李四光等人多次勸駕,都被婉拒。1953年12月1日,汪籛帶著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副院長李四光的親筆信,來到陳寅恪家中,勸說他接受委任。
陳寅恪說:「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
接著,陳寅恪提出自己的任職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牽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怎樣調查也只是這樣。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
這便是日後學術界盛傳的《對科學院的答覆》。當然,對於陳寅恪所提條件,中共肯定不會答應了。陳寅恪去北京赴任之事,最終不了了之。
汪籛殘存一些陳寅恪影響
汪籛自告奮勇南下廣州做的事,卻以失敗而告終,肯定在他心中投下濃重的陰影。畢竟,陳寅恪是海內外景仰、德高望重的學術大師,居然不再承認他是自己的學生。而他們師生當時最大的分歧是在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上。
此後,汪籛雖然繼續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他的歷史研究,但是,在此過程中,也多多少少保留了一些陳寅恪倡導的治學方法。1964年前,他招了幾屆隋唐史研究生。
他要求青年教師和學生,學習中國古代史,必須練好基本功。他很反對有些人典章制度沒有弄清楚,時間、地點、人物、事件都沒有搞清楚,就寫文章。在歷史事實的考據上,他要求青年好好向前輩學習。
他撰寫的《隋代戶數的增長》、《史籍上的隋唐田畝數非實際耕地面積》、《史籍上的隋唐田畝數是應受田數》、《唐代實際耕地面積》等論文,考訂紮實,邏輯縝密,即使今天讀來,仍足當古代史研究之典範。
汪籛還接受出版社委託,審閱了不少文稿。他對沈起煒著《隋唐史話》不僅逐字逐句進行了推敲,而且核對了所有材料。對《辭海》隋唐職官部份的條目,他也根據《唐六典》、《舊唐書‧職官志》、《新唐書‧百官志》等,逐條進行研究,全部改寫一遍。
對《魏徵傳》的譯文和註釋稿也遵照中華書局的要求,按時完成了的審閱,並為再版的《魏徵傳》撰寫了《魏徵年表》。
他本來還準備用幾年時間完成關於均田制、唐太宗、武則天的研究,以及完成中華書局委託的《貞觀政要註釋》和《唐六典校注》的審校工作,可惜都沒有能夠完成。
汪籛對馬克思主義的崩潰
然而,隨著毛澤東一遍又一遍念「階級鬥爭」的金箍咒,整個中國歷史,都變成了「階級鬥爭史」,變成了為中共政治鬥爭服務的工具。1958年,毛澤東發動第一次所謂的「史學革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甚至科學家、文學家,都被說成是「統治階級的代言人」。
1963年,毛澤東發動第二次所謂的「史學革命」,把帝王將相統統趕下歷史舞台。1965年11月,毛澤東支持姚文元等人「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用「天下烏鴉一般黑」和「剝削和掠奪是地主階級的本性」打倒一切。寫《海瑞罷官》的歷史學家吳晗等受到猛烈批判。
所有這些都對汪籛信奉的馬克思主義形成強烈衝擊。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中,汪籛因反對浮誇學風受到批判,不僅精神上受到很大打擊,而且嚴重摧殘了他的健康。1966年3月16日,汪籛受邀參加《新建設》編輯部召開的關於「讓步政策」問題座談會。
但在7天後,1966年3月23日,《光明日報》發表文章,點名批判他1953年寫的《唐太宗「貞觀之治」與隋末農民戰爭的關係》,給他當頭一棒。1966年5月,被毛澤東斥責為「閻王殿」的中宣部副部長陸定一與彭真、羅瑞卿、楊尚昆打成「彭羅陸楊」反黨集團。
汪籛曾參加陸定一策劃出版的《魏徵傳》的審閱工作。陸定一被打倒,汪籛頓感大禍將臨頭。從1950年加入中共,到1966年歷史學界發生的一切,與他曾經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馳。
想當年,他跟陳寅恪先生做研究,那是在最高學術殿堂,享受最高品質的學術生活,師生關係,亦師亦友亦家人。現如今,一場運動接一場運動,一批又一批最優秀的中國知識份子挨整,恩師陳寅恪最珍惜的學術自由已蕩然無存。
曾經,陳寅恪的弟子是下跪給老師請安的,現如今,他的學生居然把「深揭猛批」他的大字報,貼到他的家門口了。不僅如此,代表黨組織的工作組竟然那樣羞辱他。
汪籛以死做最後的抗爭
汪籛可能漸漸明白,他的恩師陳寅恪當年為甚麼如此決絕的反對用馬克思主義指導歷史研究了。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徹底絕望,促使他走上了人生的不歸路。他只能以死來證明其師陳寅恪提出的「思想自由、精神獨立」了。
據說,汪籛死的很慘。沒有稀釋的殺蟲劑敵敵畏毒性非常大。當毒性發作時,汪籛痛苦的高聲狂叫,以頭撞牆。等有人撬開了門進去時,發現他已經死了。
結語
汪籛曾經在中國最著名學者的指導下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受到過非常嚴格的學術薰陶。在時代大潮的影響下,他轉向中國共產黨,轉向馬克思主義,以為找到了一條新的路。但是,從1950年中共開始對知識份子進行思想改造,一直到1966年文革爆發,汪籛經歷了中共不斷迫害知識份子、不斷毀滅傳統文化、不斷向極左轉變。
汪籛1949年前和1949年後受到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教育,身處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環境,在他的頭腦中引發的矛盾、衝突、鬥爭,漸漸達到不可調和的程度。尤其是,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他也是在努力緊跟形勢,但是,怎麼跟也跟不上,最後,他成了被批判、被侮辱、被蔑視的對象,以至於完全看不到出路。
中國傳統知識份子講「士可殺,不可辱」。在內心的衝突不可排解之後,他只好一了百了。這是當時中國許多知識份子的共同心態,共同走過的路。這是中國當代史上最悲哀的一頁。
根子在於中共的本質是「假、惡、鬥」。唯有認清中共的本質,決裂中共,中國知識份子才可能打破精神枷鎖,走向新生。◇
------------------
🏵️《九評》20周年
https://hk.epochtimes.com/category/專題/退黨大潮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