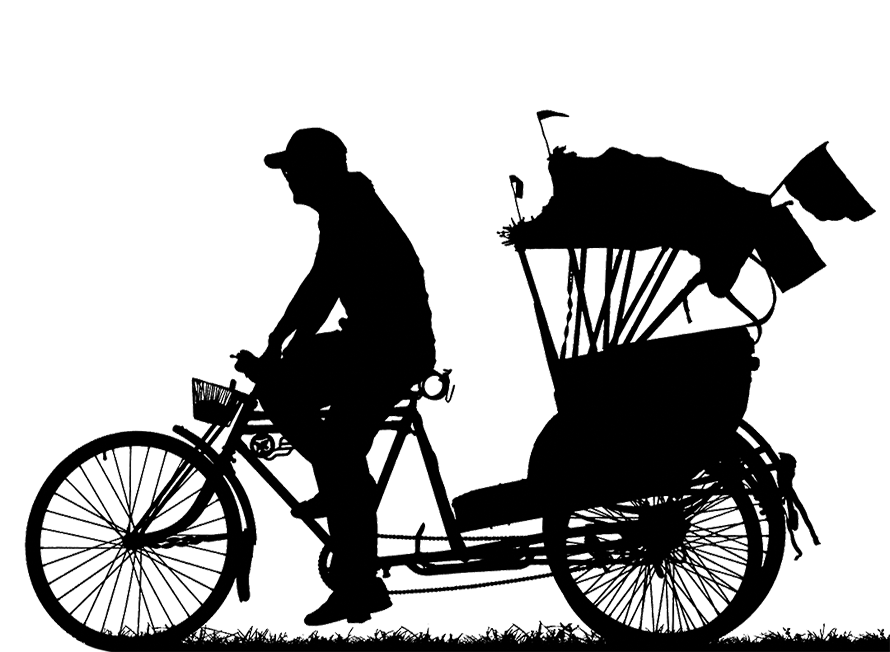改造
我成了一個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右派份子。我除了參加樂隊的工作,還必須做一些日常的勞動,如掃地、打掃廁所、倒垃圾等。每年夏種、秋收,要和其它單位的右派一起,下鄉勞動改造。
我最願意去農村勞動了,雖然生活艱苦一些,累一些,但精神上沒有壓力,你只要埋頭苦幹,不惜力,老鄉就會認同你,叫你老李。
有次,母豬快下崽了,我主動提出晚上和衣睡在豬圈,靜候豬一有動靜,就立刻去叫醒老農。半夜,豬哼哼起來,我趕緊去叫老農,結果一胎下了四個肥肥的小豬崽,把老農樂得嘴都合不攏了。直叫我老李、老李,好樣的、好樣的!
我交了好幾個農民朋友,至今還有聯繫。可是在本單位勞動,你必須低著腦袋,不敢抬頭,人們都以一種鄙視的眼光看著你,即使過去談得來的同事,也像躲避瘟疫似的,掉過頭,好像沒看見你一樣。
這些,我都能理解,最令我不明白的是,作為一種懲罰,不讓我拉小提琴而讓我去打。
在我們樂隊隊員的觀念裏,無論是小提琴,大提琴,木管,銅管還是打擊樂器,只是分工,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而打擊樂器,因為音量大,對全樂曲的節奏起著很重要的作用,有時在樂曲的關鍵時刻又起著化龍點睛的作用。不讓我拉琴去打,說明領導有貶低打擊樂之嫌。
無論貶也好,褒也好,叫我幹甚麼,我一如既往,要把它幹好。沒有人教我,我只有自己鑽研、琢磨。我看見電影裏,外國交響樂團打的演奏員,當在關鍵的樂段打時,總是要站起來,兩片銅不是對敲,而是錯開來敲,而且將兩片舉得高高的,不斷地晃動,以達到餘音繚繞的效果。
那年,我參加了舞劇「寶蓮燈」打的工作。主要演員三聖母,在她打開窗戶,讓燦爛的陽光照進她的閨房這一場景中,她興奮地翩翩起舞,臨空一躍,此處有一下關鍵的聲。
我準確無誤地,起立,揚起了兩片銅,將鏗鏘有力,又盪氣迴腸的聲,漂漂亮亮地送到了空中。排練結束在後台,飾三聖母的演員問:
「今天這是誰打的?和從前大不一樣,好像要將我托起來,飛向天空的感覺。」
指揮告訴她,是那個右派李科林打的。她低聲說:
「右派怎麼的?打得好就是好。」
從此,無論是指揮、演員、樂團演奏員,對我的工作、演奏、勞動,都很支援。
翌年,柬埔寨親王西哈努克來華訪問,國宴後,周恩來邀請西哈努克觀看民族舞劇「寶蓮燈」。緊張的排練工作開始了。一個困擾著樂團領導的問題,提出來了。
中共有紅頭文件明文規定:右派不得進入人民大會堂。 李科林不是人民,是人民的敵人,是絕不允許進入人民大會堂的。
樂團黨支部開會研究了幾天還是沒法解決,只好將這一棘手的事向院領導反映,院長不屑一顧地說:
「誰還不會打一個,找個人替一下!」
當這一換人打的事,領導和指揮商量時,指揮堅決不同意換人,並表示,如果領導執意要換人,他無法指揮。
這事迅速傳到舞蹈演員那裏,飾三聖母的演員也表示,如果換人她也不跳了。
一個指揮不指,一個主要演員不跳,這台戲就沒法演了。這下可難住了領導,只好將這一矛盾上交,彙報到文化部。
我萬沒想到我這個小小的右派居然興師動眾,驚動了文化部。文化部領導問:
「那個右派改造得怎麼樣?」
黨支部書記答曰:「工作,勞動都表現得不錯。」
部領導說:「那就特批他進人民大會堂參加演出,不過,要給他規定三條紀律:1,演出休息,只准他在後台,不得四處亂串。(因為那時物資匱乏,只要一說去大會堂演出,大夥都憋足了勁兒,拿出平時的積蓄,去小賣部大大的採購進口香煙,名酒,巧克力之類的) 2,演出結束,首長與貴賓上台與演員,演奏員握手,照像,不准他與首長和貴賓握手,更不得與首長一起照像。3,這次演出是國事任務,很重要,只准打好,不准打壞。」
樂團領導如釋重負,回來向我下達了這三條有如聖旨般的指示。前兩條,我可以百分之百的做到,即使你准許我去搶購, 我也不會那麼不識時務地去湊這個熱鬧。第二條,不用說,更不敢去和首長,外賓握手照像了。可第三條,只准打好,不准打壞,卻令我心驚膽顫。萬一因為緊張,或不小心出了錯,豈不是故意破壞國事演出的反革命罪行了?
我懷著一顆惶恐而顫抖的心,進入了人民大會堂,參加了這次特別批准的演出。
平日,我打從不看譜,音樂的旋律,已深深印在我腦海裏。可這次演出卻非同小可,這第三條規定就像緊箍咒似的,箍緊著我的大腦,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自己:可千萬別打錯了。
演出順利地進行著,三聖母就要開窗了,要騰飛起來了,我的心也隨著那愈來愈逼近的關鍵的一下而加快,都快蹦出嗓子眼兒了。我全神貫注地, 兩眼目不轉睛地盯著每一個音符,既忘了站起來,又忘了錯開打,更沒有晃動兩片,竟打出了一下從未有過的又乾、又無力的兩塊金屬碰撞聲的啞。
指揮頓時皺起了眉頭,樂隊隊員都回過頭看,以為是換了人。
我真是無地自容,就等著演出結束後的批鬥會了。
演出結束,在後台,飾三聖母的主角大發雷霆,氣勢洶洶,聲色俱厲地:
「今天這個是怎麼搞的?簡直要把我從空中拽下來,這是誰打的?」
人們告訴她還是那個右派打的。她居然沒有繼續發火,若有所悟地說:
「哦,他可能太緊張了, 太緊張了。」
觀眾們都在那裏欣賞舞劇演員優美的舞姿,誰也沒有聽出那一聲致命的啞。在指揮、樂隊隊員和舞蹈演員的諒解、同情下,我算是矇混過關了,老天保佑!
瘋狂的大革文化命
毛澤東發動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真是史無前例,攪得全國,各級政府,各行各業,直到每個家庭都亂成一團。幾千年傳承下來的優秀文化、古蹟,付之一炬,忠孝、禮義、誠信,毀於一旦。
在這種社會秩序癱瘓的情況下,說拉出去鬥就拉出去,說遊街就遊街,說打死就打死,說轟下鄉就轟走。這一無法無天的所作所為,居然美其名為有階級感情的革命行動。兩派武鬥,都標榜自己是毛澤東革命路線忠實的維護者。
人的生命都得不到保障。不要說普通老百姓,即使是國家主席也在劫難逃。
在這一片紅色恐怖的氣氛中,我這個五七年的老牌右派, 在鬥爭、批判指揮時,也拉我上台陪鬥。跪在台前, 脖子上掛上用鐵絲吊著的壓舞台天幕用的重磅鐵砣,幾小時的鬥爭會下來,都勒出一道血印了。
除了這一次算是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外,我卻過著一種逍遙的旁觀者的生活。
當時造反派成立了各種五花八們的司令部、戰鬥小組,甚麼紅旗、砸三舊、風雷擊等。他們奪了黨的領導權,過去的領導都靠邊站,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聽候審查、批判、交代。
造反派的頭頭告誡我:
「你不得參與運動,不許寫大字報,也不能看大字報,好好勞動,你的右派問題將來我們會給你解決的。」
我聽了半信半疑,造反派有多大權力?會不會也像五七年那樣,被引蛇出洞,讓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狂熱起來,推翻黨的領導,然後將來被扣上反黨份子的帽子一網打盡?
雖然根據我對過去運動的教訓,心存疑慮,但有人肯為我的事,解決問題,我還是很高興的。
我每天的勞動就是蹬三輪去買漿糊,供造反派們貼大字報。當時全市各單位都在鋪天蓋地的寫大字報,漿糊脫銷,於是不法商人就在麵粉裏摻石灰,黏性極差,貼上的大字報一乾,一陣風就刮跑了。造反派們為了有好漿糊用,也不跟我瞪眼了,盡和我說好話,要我為他們這一派買麵粉多一些的漿糊。
為了尋找品質好一些的漿糊,我不得不起個大早,蹬起三輪,到很遠的地方去搶購,去晚了就被別人買光了。
每次我買漿糊回來交給造反派們時,他們都好像是餓急了的饑民似的,一擁而上,拿著小桶拚命將自己的桶裏盛滿,趕緊拿去張貼甚麼最新、最高指示,我趁他們搶漿糊顧不上監督我的時機,偷偷回頭迅速地瞄了一眼大字報,在我的右側,醒目的大字報寫著:
「xx走資派必須低頭認罪!」
這不是我們的書記嗎?怎麼你也犯罪了?
我看了大字報,心中有種說不出的滋味,是同情?是幸災樂禍?還是僥倖自己好在沒有入黨?
我的另一個工作就是:為雙方造反派揪出來並關押起來的人送飯。
他們都被扣上所謂「反動份子、特務、歷史反革命」以及「攻擊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現行反革命份子」等帽子。
造反派頭頭告誡我:
「不得為他們傳遞資訊,飯菜的標準只能買最便宜的青菜、豆腐,不得買雞、鴨、魚、肉。」◇(待續)
-------------------
局勢持續演變
與您見證世界格局重塑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