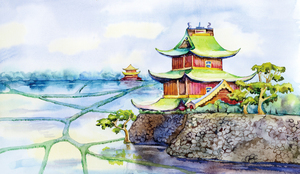拿起那塊涼涼的瓷片,放進口袋裏,思索片刻,又放回了土裏,將地面也填平了。望著遠處的景德鎮,黃昏已將迷濛的市街鋪上了一層琥珀金黃,那是從遠古鋪來的顏色。忽然想起父親說的:「瓷器這條路,遠呢。」現在我才領悟父親這話。
這棵高大的槐樹下面,碎瓷片排成的「箭」字符吸住了我的眼光,順著箭頭望去,指向前面的山谷,瓷片上還有坊號的淡藍色雲朵釉彩,看得出來,這些瓷片就是咱「如意坊」廢棄的碎片,定是父親特意留下的記號。拿著手上父親交給我的地圖,仔細對照眼前的山川地勢,心想,只這張祖輩傳下來的泛黃的地圖還管用。
至於那個下午,當我泥土玩得正起勁時,父親站在窯邊喚我過去,蹲下來輕輕抹去我臉上的土灰,「不能整天玩泥土了,該到鎮上找個教書先生好好讀兩本書。」父親嚴肅地說:「瓷器這條路,遠呢。」到現在,仍然覺得這話說了等於白說。
後來我也沒有進到課堂,卻走了做瓷的路。那天,瑞瑞小師傅提著瓷鐘把我從酣睡中敲醒,一張笑臉對著我:「快,咱們鎮上瓷器街逛去,我跟爹告了假了。」然後轉過頭去,指著長壁邊一排瓷坯前的孟師傅,孟師傅肩上還掛著白汗巾,向我舉著高頸瓷酒瓶,我站起來,墊起腳尖朝他揮手。
瑞瑞整天是孟師傅的小跟班,高了我一個瓷碗高。跟著他跑出坊門,我們從南城樓一路奔到鎮上這條陶瓷大街時,街道上正熱鬧著。那年齡,這鎮叫甚麼名字我也不去理會,紅紅綠綠的人群才是我最喜歡的。
這時,前面一頂高轎子,被兩個亮著胳膊的漢子抬著向我盪過來,抬轎漢子的吆喝聲穿透人群。正看在興頭上,瑞瑞卻一個勁把我拉進了一家陶瓷鋪裏。
偌大的鋪裏滿坑滿谷都是陶瓷器皿,擺滿牆櫃、木架子,連地上都擺了。我發現地上一個大缽盆裏,一隻鴨子正優遊水波間,漣漪片片,粉紅蓮花在細枝上燦爛搖曳。我好奇的蹲下來看時,原來是師傅畫的,驚訝地叫著瑞瑞,卻沒有回應,搜尋鋪裏四周,只有三兩顧客,卻不見瑞瑞蹤影。
走出鋪來,只見街道兩旁擺滿了地攤,一路伸至大街盡處,都是賣的陶瓷器。眼前這家賣的是破碎瓷片,瓷片上還標了價格,越看越有趣。那個白鬍子老闆還拿起一塊塊瓷片跟我解說,這是哪個朝代的,那是哪個朝代的,還講了瓷片的故事。我只記得他講的瓷片多珍貴,把那些朝代給忘了。
瞧這街道可是車水馬龍,人聲馬蹄聲車轂轆聲混成一片,可比咱如意瓷坊熱鬧多了。我興奮地一家家逛去,只見著各種各樣的瓷器,早把瑞瑞小師傅給忘了,待將視線從攤上那座高大的彩繪牡丹瓷瓶拉回來,抬頭只見遠處天空貼著一顆橘紅太陽,已不知身處何處了。
一路遊蕩過去,走到橘紅色太陽底下時,暮色裏幾家屋舍都上了燈了。原來,走進城鎮北邊的村莊了,瞧村口這戶人家,屋簷下掛著一隻白瓷宮燈,黃色燈火在風裏飄盪著溫暖的輝光。
「可不是城裏如意瓷坊小兒子嗎。」有個大嬸在宮燈下朝我喊著,一時想起父親說過這村裏有個收藏古瓷的人家。大嬸不停地喚著我:「這孩子進屋裏來啊,我們家的碗兒可等您多年了。」於是,我從白瓷宮燈下走進了屋裏。
「孩子,我給您盛上一碗大米飯,吃了晚餐,在這兒好睡一宿。咱兒子跟他爹上山採藥去,等月亮爬上窗前他們就回來了。」大嬸端著一隻大瓷碗放在桌上,碗裏是尖尖的白米飯,冒著白煙,桌上還擺著兩碟小菜。一時,飯香在屋裏散發開來,我兩口吃了碗裏的尖山,就整晚瞧著那碗兒,手指摩娑著那碗上淡青色釉彩,等著窗前的月亮浮上來。
記得月色裏,我拿起筷子輕輕敲著瓷碗邊緣,清亮的聲音迴盪屋裏,穿透窗戶,碰著了絲絲絃音時,內屋傳來大嬸的聲音:「採藥的男人回來了。」片刻,又傳來一句:「孩子啊,記得明兒把那碗兒帶回去啊。」
一夜沒回家,記得回到坊裏,心裏忐忑地將瓷碗拿給父親時,父親雙手捧著那碗,睜著眼睛看了半響,甚麼也沒說,或許說了我也不懂,只輕聲唸著:「是個好碗。」又說:「你再跑一趟,拿兩個咱那老瓷瓶兒,給城北留德莊這大嬸送去。」
一直到現在,當月亮升起時,我總會聽到那輕敲瓷碗的清亮的聲音,就是那聲音,引著我走進了瓷器的世界。
第一次,我捏的是一隻瓷葫蘆,坊裏師傅們都給我掌聲,瑞瑞小師傅手掌拍得最響,我知道大夥兒給我鼓勵,我當然很高興。
想起小時候,在坊裏玩膩了,一個人跑到河邊挖紅黏土,把土裏的枝滓殘渣拿掉,耐心的拿石頭搥打黏土直到變成圓球,將大拇指插入球裏,拉成粗粗的罐子,再撿乾木柴升起火,把泥球燒燙了,冷了後才發現泥罐子滿身都是小洞洞。現在能燒出一隻瓷葫蘆來,雖然笨笨歪歪的,確實打從心裏興奮。
坊裏大夥正忙著,幾位師傅肩上扛著坯板,都疊了兩層,坯板上擺滿瓷坯,挺著腰桿從我身邊過去;另一邊過道,一台輪車裝了兩個大缸坯,兩個師傅護著,車輪子擠鼓擠鼓地向窯爐滾去。
我喜歡遊走坊裏各處,這邊地上錯落著幾個師傅,或蹲或坐地上。一個師傅拿著毛筆將藍色染上瓷壺,我好奇地蹲下來,那師傅又塗上黃色釉料,壺身就停了一隻展翅大雁。彩繪師傅抬頭看了我一眼又低頭工作。這時,我耳朵被捏了兩下,是父親,父親彎下腰來,向那師傅說:「大雁的翅膀色彩要有深淺,這是重要關鍵。」那師傅領會地點點頭,我瞧著他拿起筆抹了幾筆,果然大雁飛了起來。那師傅滿意地站起來,被父親按著肩頭:「雖是細節,用心了就是工夫。」父親看了我一眼,轉身走了。我坐在地上,斟酌著那壺上飛翔的大雁,耳朵仍留著餘溫,是責難也是鼓勵。
坊門口,一排師傅挑著泥土魚貫走進來,向窯爐跑去。我遠遠地瞧見了,孟師傅站在那座古窯邊張望著,瑞瑞跟在後面,想是這幾日要燒窯了,坊裏就熱鬧了。
父親已站在磚台上那半身高的瓷器佛像前,仰頭凝視著,我抱著粗粗笨笨的瓷葫蘆走過去,心裏想著,這埋藏地下的泥土經過了多少歲月滄桑、千百年風霜雨雪,終於被捏成了瓷器。
過後幾天,村人挑著一擔擔木柴進坊裏來,都是剖開的白白的木柴,堆放在那座古窯旁邊。然後,一個大青花瓶瓷坯由兩位師傅合抱著,直接送進古窯爐裏,接著,幾位師傅動作輕快的,挪動磚牆將窯口堵住了,又在窯體四周抹上了濕泥土。
師傅們還是忙著手上的活兒,只是靜得可以聽見心跳的聲音,「燒起來了。」有人輕聲說著這話。瑞瑞走到我身旁,也是嚴肅的表情:「這是試窯,過幾天就要正式燒窯了。」又輕手輕腳的向窯邊的孟師傅走去。
幾天後的黃昏,古窯爐被打開了,空氣還是凝固著,師傅們望著窯口,臉上的表情都是期盼。又忍了一天,窯爐冷了,第二天太陽還沒出來,那青花瓷瓶坐著台車被推出了窯爐,這一刻,師傅們盼來的是驚呼。
大夥圍了過去,孩兒高的青花瓷花瓶還在冒著汗,幾顆水滴沿著瓷身滑下來,我亮著眼,看著挺立眼前的瓷瓶,讓我想起市街上腰姿綽約的村婦,耳朵裏都是師傅的驚嘆聲。
我擠在師傅裏邊望去,父親在瓷瓶前欣喜的向孟師傅點著頭,瑞瑞站在孟師傅腳邊仰頭望著他們。
村人又陸續挑著木頭進來,坊裏也跟著忙碌起來。師傅們將大大小小、圓的扁的各種磁坯,井然有序的送進窯爐裏,孟師傅站在窯口招呼著,瑞瑞繞著孟師傅奔奔躥躥,比誰都忙,這次是真的熱鬧了。
忙了兩天,古窯爐口上了磚門,緊鄰的大窯也被掩閉了。此時,時間似乎慢了下來,師傅們散開了,回自己工作位置上去。我看見父親從坊場那端走來,跟周圍的師傅們打著招呼,一面向窯爐邊的孟師傅揮著手,孟師傅瞧見了,在空中揚起手來。
「窯裏燒起來了。」這話在師傅群中細聲傳著,聲音帶著希望跟期盼,我好像又看到那座站在古窯口,腰姿綽約的青花瓷花瓶,也看到了第一次捏的笨葫蘆。
窯燒的一天夜裏,在睡夢中被一股濃烈的酒味嗆醒了,我靠著磚柱子從窗戶望出去,一彎月亮高高掛在天空。是秋天了,天氣轉涼了,師傅們都披上了厚衣裳。前面,地上放了幾瓶酒,幾個瓷杯子躺在酒瓶邊,才發覺,師傅們徹夜守著窯爐,父親抱著兩瓶酒放到他們身旁。
靠著柱子,瞧見遠處窯爐邊,有人往窯洞口添加木柴,點點火花在夜色裏跳竄著。我在興奮中等待著開窯,心裏想著,那長久埋在地底的泥土,會被師傅們變成一個個甚麼樣兒的瓷器。那一年窯燒的心情,我一直藏到現在。
那天,趁著等待開窯時刻,父親帶我登上了南城門後方小山,他說:「咱坊裏每年年尾燒瓷器,這窯燒總要個把月。」
我們站在山頂,父親望著前面整齊的市街:「那是咱景德鎮。」然後轉向右邊,指著遠處悠悠的說:「有條小河流過城郊,那就是河岸的碼頭。」
父親說,燒好的瓷器要搬到靠碼頭的長竹筏上,然後劃過一段小河,送到大河裏,來來回回要好幾十趟,總要三、四個白天連著夜晚才能搬上大船。船上、竹筏上還要有人看管,流程中都得要細細心心,父親說,這是一個重要的過程。他將視線收回來:「一年裏,燒好的瓷器總有個千來件吧,往年都裝了兩條大帆船,運往北方大城市,咱如意瓷坊早有了口碑了。」
聽著有趣了就問父親:「船上要許多人照管吧,我真想去。」「每年都是孟師傅帶著十幾個師傅護運瓷器,都是順順暢暢的。」父親看著我,酸酸的說:「孩子,多玩幾年再說吧。」
而我一次也沒上過船,只能想像浪裏飄盪的船兒,船帆在風裏飛揚的好樣兒。
我雖然沒上過運瓷的大帆船,可現在卻攀上了峰嶺山頂,尋到了瓷土。看著腳邊潔白的瓷土,我收起地圖,蹲下來欣喜的抓起一把瓷土,輕輕搓揉著,粉末從指間飄落,一時,想起父親說的:「就是白白的,沒一點兒顏色。」我興奮地站起來環視四周,遠處是翠綠的連綿山峰,前面有一條小徑蜿蜒而去,然後隱入荒草裏。
雖然這裏離景德鎮越遠了,可還看得出模糊的市街,前邊腳下的村莊反而清晰了,那可不是留德莊嗎,望著廣闊的藍天,山上的風陣陣吹來,讓我想起藏著古瓷器的大嬸,想起簷下掛著的白瓷宮燈,黃色燈火是否仍在風裏搖曳。
蹲了下來,讓手指鑽進瓷土裏,涼涼滑滑的感覺沁透胸懷,一時,心裏升起尋著了寶的興奮。這時,指頭感覺碰著了硬硬的東西,小心翼翼的從土裏拿了出來,低下頭仔細瞧時,發現是一塊破瓷片兒,旁邊還埋了一堆,都是破了、裂了的瓷片。
我將瓷片的土灰塵垢抹乾淨了,漸漸呈現出焦黃色澤,仔細瞧那瓷片剖面卻仍潔白無瑕。手指珍惜的在瓷片上摩娑著,感覺有線條紋路,拿近瞧時,原來鐫了字兒,那字體像蚯蚓般溜來溜去,還好我認得一個字兒,是「景」字,另一個被削去了一邊,只留下半個字,讀書識字的人定能辨出字兒來,我只能猜想,是個「德」字吧。
我拿起那塊涼涼的瓷片,放進口袋裏,思索片刻,又放回了土裏,將地面也填平了。站起來,放下身上的包包,遙望景德鎮市街,忽然想起父親說的:「瓷器這條路,遠呢。」現在我才領悟,父親這話沒有白說。
望著遠處的景德鎮,黃昏已將迷濛的市街鋪上了一層琥珀金黃,那是從遠古鋪來的顏色。此時,眼前又出現瓷片上彎彎曲曲的文字,或許在遙遠的歲月裏,這裏也有過一個製作瓷器的叫「景德」的城鎮。
可是已找不到父親去問了,卻想著山下留德莊那位大嬸來了,想著,去吃一碗大米飯,在月光下,靜靜聽著輕敲瓷碗的清亮的聲音,那從久遠的泥土裏傳來的聲音。◇
-------------------
局勢持續演變
與您見證世界格局重塑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