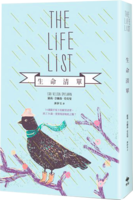我希望在世上留下足跡。
我希望贏。
不,這麼說不對,應該說我不想輸。
然後奇蹟出現了。我年輕有力的心臟開始怦怦作響,粉色的肺葉如鳥翼般向外開展,樹木模糊成一大片綠色背景,我要的人生完整地浮現在我眼前:比賽(play)。
是的,沒錯,就是它了。快樂的秘訣(我向來懷疑有這玩意)、美與真的本質(或者我們終其一生只須知其一)會在生活的某刻冒出來,可能在球劃過半空中的那瞬間,可能在兩個拳擊手等著裁判按鈴,可能在跑者快接近終點線時,可能在群眾不約而同整齊劃一站了起來。勝負決定前那扣人心弦的半秒鐘,心情激動興奮、感受涇渭分明、影響重大深遠。
這就是我想要的東西,不管它究竟是甚麼,我希望人生與日子就是那樣。
有時我會幻想自己是偉大的小說家、傑出的記者、優秀的政治人物。但不管從事甚麼職業,一流的運動員始終是我的終極夢想。
可惜天生沒這個命,我的運動細胞雖然不錯,但稱不上一流,直到二十四歲終於認清了這個事實。我以前參加過奧勒崗的田徑賽,表現不俗,四年內有三年都拿獎。但就這樣了,再無突破。
今早我輕快地跑完一趟又一趟六分鐘的距離。看著冉冉升起的太陽將路邊松樹最下層的針葉曬得火熱,邊跑邊問自己:有沒有可能不當運動員就能經歷和運動員一樣的感受?可以一天到晚比賽而不用工作?有無可能熱愛工作到甚至把工作視為競賽?
世上到處是戰爭、苦難,人們每天被苦差搞得又累又不平,我認為懷抱偉大的夢想也許是脫離苦海的唯一出路。這夢想有實踐的價值、有趣好玩、和自己的能力與興趣相符。有了夢想後,學習和運動員一樣──心無旁騖、全力以赴、從容應戰。不管喜歡與否、同意與否,人生就是比賽。任何人否認這事實或是拒絕參賽,就只能站在邊線觀戰。要我做甚麼都可以,就是不要這樣的人生。
說到人生,一如既往,每次都走到同一個結論:「瘋狂點子」(Crazy Idea)。我心想,應該再重拾一次我那個狂想,也許它會成功?
也許吧。
我愈跑愈快,彷彿在追人,也彷彿被人追趕。奈特狂想會成功,我向天發誓,我會讓它成功,不容任何失敗的可能。
我突然笑了,幾乎大笑出聲。全身是汗地繼續往前跑,一如既往,步履優雅又輕快。狂想閃耀於眼前,呼叫著我,我心想,這狂想沒那麼瘋狂啊。其實它連想法也稱不上,倒像是某個地方、某個人,在我擁有它之前就已活生生存在了,和我既是兩個分開的個體,又好像是我的一部份。這聽起來也許有些文縐縐、有些瘋狂,但我當時就是這麼想。
話說回來,我當時也可能沒那麼想。也許我的記憶誇大了「啊哈,有啦!」的心情,將多次興奮激動的時刻一古腦湊在一塊才會如此。但說不定真有這樣的時刻,類似跑步人跑到某個距離後產生的愉悅感(runner’s high)。總之我不知道,也說不清楚。那些年、月、日就這麼過了,慢慢自理出頭緒,宛若口鼻吐出的白色煙圈,消失於無形。臉孔、數字、決定這些原本以為會跟著自己一輩子、永世不變的東西,如今全消失了。
經過淘洗,最後留下的是泰山崩於前不改其志的篤定,以及永不消失的核心真理。二十四歲時我的確有一個狂想,儘管和其他二十郎當的年輕男女一樣,難免會隨波逐流、人云亦云、對未來充滿恐懼,但當時我真的認定,瘋狂點子打造了這個世界。歷史是狂想串起的長河。我的最愛──書籍、運動、民主政體等,都始於狂想。
說到瘋狂,鮮少想法的瘋狂程度可和我最愛的跑步相提並論。跑步辛苦、痛苦、還有風險,回報卻少之又少,也完全不保證付出努力就有收穫。不論是跑在橢圓形的跑道上,還是跑在空曠的路上,並無真正的終點或目標。
跑步時,找不到一個可讓努力與付出完全站得住腳的理由,那麼為何要跑?說穿了,跑步本身就是目的。跑步沒有終點線,完全由跑者自訂終點。不管跑步得到的是苦還是樂,你必須從跑步本身去尋去探究,是苦是樂完全看你如何型塑跑步,看你如何說服自己踏入跑步的世界。
每個跑者都知道這點。你持續地跑,跑完一英里又一英里,但你從來不去追究自己何以會如此。你告訴自己,你是為了某個目標而跑,為了趕上甚麼而跑,但實際上你是因為不敢停而持續地跑,因為停下腳步讓你害怕得要死。
因此一九六二年的那個早上,我告訴自己:就讓別人說我的想法瘋狂吧……繼續跑下去就對了,永遠別停腳。甚至連想都不要想,直到抵達那兒,千萬不要把過多注意力放在「那兒」是哪裏。不管碰到甚麼,繼續跑下去就對了。
這是我深思熟慮後得出的道理、洞見、心得。不知怎地突然想通這點,然後逼自己盡量接受這樣的指點。過了半世紀,我深信這是最好的勉勵,也可能是我們能給其他人的唯一建言。◇(待續)
——節錄自《 跑出全世界的人》/ 商業周刊
-------------------
局勢持續演變
與您見證世界格局重塑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