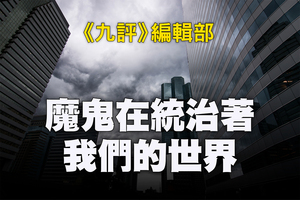前言
上世紀初,魔鬼安排其人間代理蘇共以暴力奪取政權,同時為其在世界舞台的最後一出大戲的主角做了鋪墊——這就是當時由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一手建立的中共。此後數十年間在國際舞台上扮演主角的是蘇共,和西方自由陣營正面對抗的是蘇共,西方人也一直以蘇共和東歐共產黨為樣本來認識共產主義。這給了中共充份的時間發展壯大。
上世紀90年代初蘇共解體,中共登上國際舞台替換蘇共唱主角,用難以察覺得非暴力方式利誘人們與之共舞。此時的中共搖身一變,宣稱不再糾結意識形態之爭,而以「改革開放」的旗號極力擁抱全球化、發展極權制度下的權貴資本主義經濟。許多西方學者、企業家和政客們因此並不把中共當作共產主義政黨看待,至多認為它是一個「另類」的共產黨。
但事實上,中國共產黨集中了共產主義的「假、惡、鬥」和人類幾千年政治權謀中最狡猾最陰險的部份,用利益誘惑人、用權力控制人、用謊言欺騙人,把這些魔鬼的工具掌握得爐火純青,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中國擁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和輝煌的傳統文化,世界上很多人具有很深的中國情懷,對那片古老的土地和中國人民抱有好感和敬意。中共充份利用了這一點。在其篡取政權後,綁架了中國人民和整個國家,混淆「中共」與「中國」的概念,把自己的野心隱藏在中國「和平崛起」的外衣下,這也構成了國際社會識別中共的難度。
但萬變不離其宗。中共的經濟合作策略只是為了用「資本主義肌體的營養」[1]養肥自己的社會主義軀體,為穩固其統治、實現其野心服務,並非為了中國真正的繁榮富強,其具體做法處處與普世價值相悖。
人類正常國家的立國之本來自於歷史上的先哲、來自對神的信仰,要求遵循創世主所定下的行為規範、保持高尚品德、保障私有產權、恪守普世價值。正常社會的經濟發展也都要有相應的道德水準支撐。魔鬼有意在中共黨國裏反其道而行之,在中共道德最敗壞時,打造了一個快速崛起的「經濟怪胎」。邪靈安排這場「經濟奇蹟」的目的很簡單:沒有經濟上的強大,中共就沒有對世界的發言權。邪靈並不是為了中國強大而安排這一切,而是要利用人對金錢和財富的崇拜,讓全世界在經濟上和國際事務上有求於中共。
中共對內用暴政和資本主義中最不好的部份來運作這個體制,顛覆人類的道德,賞惡懲善,讓最壞的人在社會中最成功。其政策把人性中惡的一面放大,又用無神論造成人無所畏懼的徹底墮落。對外則極力在全球鼓吹「中國(共)特色」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利用經濟利益誘惑,讓自由世界的人們放棄道德原則、默認其在中國實行的大規模信仰迫害和人權侵害。很多西方國家的政要和大公司為了利益向中共妥協出賣良知,按中共的規則行事。
西方國家希望對中共進行和平演變,中國表面上的確現代化和西化了,但是中共的核心從來就沒有被演變過。幾十年下來,真實的結果卻是中共成功地和平蠶食了美國的立國之本和人心。魔鬼就是要在精神道德層面上摧毀人類的普世價值。
中共是共產邪靈在人間的代表,它為了毀滅人類而來。中共是當今世界文明的最大威脅。魔鬼讓中共擴張全球的直接野心是將其毒素散佈世界,並最終以強制形式脅迫人背叛傳統、背叛神。其直接的全球野心即使沒有得逞,在這個過程中人們被它用經濟利益誘惑放棄道德原則,或者被它的金融圈套勒索控制,或被它在政治上滲透,或被它的大外宣迷惑,或被它的軍事威懾恫嚇而不敢談道德原則,無論如何,魔鬼都同樣達到了其目的。
面對如此巨大的危險,人們不能不仔細考察中共的野心、策略、手法及其背後的目的。
1. 中共野心是取代美國,稱霸世界
1)中共稱霸世界的野心一以貫之
中共不滿足於做一個地區大國,而是要爭霸世界,這一點是由中共的本性決定的,是與生俱來的。中共的本質是反天、反地、反傳統的,要用暴力打碎「舊世界」,消滅國家、消滅民族、消滅階級,「解放全人類」,這註定它一定會不斷擴張,要以共產主義形態一統天下。因此,共產主義從一出現,就必然是一種「全球主義」的學說和實踐。由於傳統文化的力量曾經相當強大,在某些具體時間、地點,共產邪靈不得不採取漸進的、迂迴的方式,宣稱「社會主義首先在一國建成」,「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與西方民主國家的政黨輪替不同,中共一黨獨大,其戰略目標常常以幾十年、上百年為時間段,分步驟實現。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很快就喊出「超英趕美」的口號,搞「大躍進」,後來迫於國內和國際形勢,曾經長期採取低姿態蟄伏。「六四」屠殺之後,中共遭到國際社會的圍堵。當時中共評估形勢後認為尚無法和美國抗衡,因此提出「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的方針。這並非是中共改變了其目標,而只是在爭霸的不同階段採取的不同策略、不同姿態而已。
從另外一個層面上觀察,共產邪靈「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在全球範圍內率先扶植的是蘇聯,其真正目的是要把中共鍛鍊「成熟」,作為最後時刻毀滅人類的利器。
2)欲稱霸世界,必打敗美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也是維護世界秩序的國際警察。任何一個國家要想稱霸世界,必須打敗美國。因此,在大的戰略方向上,中共必然以美國為主要敵人。幾十年間美國一直是中共的假想敵,中共從沒放棄對美國的全方位「進攻」做準備。
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2049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秘密戰略》中分析,中共有一個長期的戰略計劃,那就是在中共建政100年時,顛覆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稱霸世界。在中共國防大學製作的電視片《較量無聲》中,明確表達了與美國較量的野心:中共在實現其主導世界的「偉業」的過程,「必然始終伴隨與美國霸權體系的磨合與鬥爭,這是一場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世紀較量。」[2]
中共的全球戰略佈局圍繞著對美戰略展開。賓夕凡尼亞大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林蔚(Arthur Waldron)2004年在國會參議院的一次聽證會上陳述:中共軍隊是當今世界上唯一一支專門對抗美利堅合眾國的軍隊。[3]事實上,不僅在軍事方面,中共的大部份外交活動、國際戰略都是直接或者間接針對美國的。
3)全方位滲透和圍堵美國
為了實現稱霸世界的企圖,中共進行了全方位的佈局。其在意識形態上和美國以及自由民主國家進行競爭;在經濟上企圖以強制技術轉讓和盜取知識產權實現「彎道超車」,用經濟發展證明「制度自信」;在軍事上和美國進行靜悄悄的無聲對抗,以「不對稱作戰」、「超限戰」為戰術基礎,積極發展軍備,在南中國海等地小試鋒芒;扶植北韓、伊朗等流氓國家,牽制美國和北約。
在外交上,中共推動「大周邊戰略」、「一帶一路」計劃,對周邊國家、歐洲、非洲、澳洲、拉丁美洲各國同時下手,迅速擴大國際影響力和控制力,企圖在國際上扶植一批附屬國,建立勢力範圍,孤立美國。中共以多種方式,在國際上合縱連橫,比如建立上海合作組織(1996)、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2015)、發起與中東歐國家的16+1合作(2012)、熱衷於金磚五國合作、大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爭取工業標準(如5G網絡)的制定權,不斷擴大影響力,爭取話語權。
與此同時,中共利用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與媒體言論自由,發動統一戰線、大外宣、諜報戰等手段,企圖最大限度地從內部操縱與和平演變美國:建立私人關係收買美國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外交官和退役軍官;用經濟利益驅使美國資本家當中共說客,來影響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強制高科技公司配合中共的網絡封鎖和信息審查;威逼利誘大多數華人社團自動成為第五縱隊;滲透美國智囊和學術科研部門,按中共的要求自律,為中共說話;收購和投資美國的媒體和電影業,同時制定「大外宣本土化」戰略,喉舌媒體大舉進軍美國本土,力圖掌握輿論,控制美國對中共的話語權……中共一方面在世界各國建立包圍美國的戰略圈,另一方面在美國本土步步為營,全線出擊,廣泛培植代理人,分裂美國社會,興風作浪日甚一日,成為美國的心腹之患。
4)長期煽動仇美情緒,為戰爭作輿論和心理準備
作為共產邪靈在人間最重要的代理人,中共從仇恨當中吸取維持其自身存在的能量。中共所宣傳的「愛國」,是建立在恨的基礎上的──「愛國」就是恨日本、恨台灣、恨藏人、恨新疆少數民族、恨獨立教會、恨異見人士等等,尤其重要的是恨美國。在中國網民之間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小事找日本,大事找美國」,意為中共政權遇到小的麻煩就煽動民間的反日情緒,遇到大的麻煩就煽動反美情緒,以轉移民眾視線。通過煽動排外渡過統治危機,這樣的事情在中國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
中共建政前曾多次稱讚美國對中國的友善和美國的民主制度,但建政之後,立刻利用中國近代的積弱和中國人急於自強的心理,挑起仇美、仇外情緒,把自己吹捧成民族的救星。事實上,中共根本不在意中國民眾的死活,也不在意中國的領土,更不在乎中華民族長遠的健康發展。中共迫害中國民眾、出賣國土、破壞道德與傳統文化、毀掉中國未來前途的罪惡罄竹難書。中共對外煽動仇恨,其真正動機有四:一、為自己貼金,標榜功勞,為其殘暴統治製造合法性;二、在遭遇困境時轉移民眾注意力,通過挑起仇恨和民族主義情緒來渡過難關;三、為中共擴張的野心做準備,把其邪惡圖謀隱藏在所謂的民族自強、強國雪恥的幌子之下;四、用仇恨為未來戰爭做輿論動員與心理準備,為毫無道德底線的非理性手段爭取最大限度的支持。
被中共灌輸了滿腦子仇美思想的青年一代,成為中共取代美國、稱霸全球的馴服工具。一旦時機成熟,中共必將利用他們,以各種手段滲透打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國家,必要時不惜發動慘烈的戰爭,包括超限戰乃至核戰。「911」恐怖襲擊發生後,中國網民一片歡呼,說明中共的這一貫穿其執政始終的宣傳戰略已經開花結果。在中國的各大時政論壇和軍事論壇上,「中美必有一戰」的叫囂不絕於耳,也是中共仇美宣傳成功的標誌。這是中共處心積慮進行的長時段、漸進式的對美戰爭動員。
中共的仇美宣傳不僅限於國內。在國際上,中共與那些反美國家沆瀣一氣,統合全球反美勢力,煽動國際仇美情緒,成為國際上仇美陣營的「精神領袖」和「帶頭大哥」。它或明或暗地支持流氓國家、恐怖主義組織與美國作對,給它們提供經濟援助、武器裝備、理論基礎、戰術培訓和輿論支持。中共是當今世界不折不扣的邪惡軸心。
5)放棄韜光養晦,對美國高調「亮劍」
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在這一年的北京,史上最貴的奧運會把一個包裝成「盛世」的中國推向了國際舞台。在全球化過程中產業逐漸空心化的美國,經濟上面臨困難,於是請求中國伸出援手,「美國靠借中國人的錢過日子」成為了中共大肆炒作的話題。「美國在走下坡路,中國將要取而代之」,這種輿論主宰著中共的媒體版面,甚至也成為了西方媒體和學界的流行看法。
2008年後,美國在經濟、軍事和政治等各方面都呈現出頹勢:經濟上,重點在推全民醫保,擴大福利,以氣候話題為執政基石,加強環保監管,扼殺傳統製造業,而新能源產業又被「中國製造」打得一敗塗地,產業持續空心化,缺乏有效措施遏制中國在貿易和知識產權上對美國的巨大傷害,消極接受「中國崛起」和美國衰退是無可奈何的現實;軍事上,開始削減軍費,主張弱勢外交;政治上,美國社會主義思潮日益興起,社會分裂加大,民主政治變成政黨利益的遊戲,動輒癱瘓政府職能。相對於中共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專制模式,美國的民主制度反而成為讓中共看笑話的反面例子。
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銀行2014年公佈的數據顯示,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當年國內生產總值或將超過美國。[4]在看到中美實力對比發生了巨大變化、以為美國衰敗之勢已不可逆轉之後,中共終於拋棄了三十多年的「韜光養晦」,要針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高調「亮劍」了。中共官方、媒體和專家漸漸口無遮攔,大肆鼓譟「中國夢」,更加露骨地表露其野心。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又於2017年舉辦「全球政黨大會」,製造「萬邦來朝」的假相,急於向世界輸出「中國(共)模式」,這種野心趨於頂峰。
目前中共提出的「中國模式」、為世界提供「中國方案」、「中國智慧」等等,打的是中國的旗號,但背後的真實意圖是中共要成為世界領袖,建立以中共政權為軸心的世界新秩序,並為此在方方面面做了長期精心的準備。這個世界新秩序如果實現,將會出現一個不折不扣的「邪惡軸心」、「邪惡帝國」。世界各國領袖和人民都面臨著一個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更為嚴峻的抉擇。
2. 中共稱霸全球戰略
1)「一帶一路」──以全球化的名義擴張版圖
(1)「一帶一路」登台
2013年中共正式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倡議。倡議稱中國將投資數千億美元,在數十個國家主導橋樑、鐵路、港口和能源建設,要打造有史以來由單個國家發起的最大規模的海外投資行動。
一帶,就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在陸地上的,有三大走向,一是從中國出發,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二是從中國西北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三是從中國西南經中南半島至印度洋。「一路」,指的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有兩大走向,一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經馬六甲海峽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二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向南太平洋延伸。
陸地上的「一帶」的主體框架目前有六大經濟走廊: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中巴、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具體地說,新亞歐大陸橋以從中國到歐洲的鐵路運輸「中歐班列」(China Railway Express)為依託。海運從中國到歐洲,花費三十多天,而通過鐵路只需十多天。中歐班列從2011年開始運行,成為「一帶一路」的重要組成部份。中巴經濟走廊是中國與巴基斯坦合作的大型工程計劃,是一帶一路的樞紐和旗艦項目,包括修建一條從新疆喀什到巴基斯坦瓜達爾港的高速公路。瓜達爾港(Gwadar Sea Port)2013年交中方營運,是巴基斯坦通往波斯灣和阿拉伯海的大門,戰略位置重要,扼守著承擔全球40%原油供應的霍爾木茲海峽通往阿拉伯海的海上通道。
海上「一路」的主體框架是共建一批重要港口和節點城市,爭奪海運控制權。對實力較強的國家,採用先參股或合作經營碼頭建立關係,對相對貧窮的國家則用經營帶動其經濟,力圖取得港口或碼頭的控制權。僅2013年一年,中國企業就至少獲得了17個海外港口或碼頭的經營權。其中,招商局港口公司通過收購法國Terminal Link港口公司49%的股權,獲得了該公司旗下四大洲8個國家15個碼頭的經營權。[5]中共這些年入股或者收購的港口還包括比利時的安特衛普港口和澤布呂赫碼頭、埃及的蘇伊士運河碼頭、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康普特(Kumport)碼頭、希臘的比雷埃夫斯港、新加坡巴西班讓碼頭、素有「歐洲門戶」之稱的荷蘭最大港口鹿特丹Euromax碼頭、阿聯酋阿布達比的哈里發港二期碼頭、意大利的利古裏亞瓦多港口碼頭、馬六甲海峽的關丹港、非洲的吉布提港、巴拿馬運河等等。除了投資,中共還通過一帶一路製造的債務陷阱獲取戰略要地。斯里蘭卡因無力償還中國公司的債務,2017年底簽署了一份有效期為99年的租約,正式將具有戰略意義的漢班托塔(Hambantota)港移交給中國。
中共2018年又提出了「數字絲綢之路」,目標是要重塑全球互聯網的未來發展。「數字絲綢之路」是一帶一路的高級階段,成為推進「一帶一路」的最新動力。「數字絲綢之路」的重點是光纖電纜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互聯網、數據信息服務、國際通信以及電子商務。很多「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沒有完備的信用制度,中共希望藉助「數字絲綢之路」把中國的電商模式和電子支付手段,比如支付寶,推廣到這些國家,把西方的電子商務徹底排除在外。封鎖網絡的「防火長城」是中共的獨門絕技,也將隨著「數字絲綢之路」走出國門,將中共的網絡控制輸出給更多國家。
中共的戰略範圍從它在全世界的基建投資規模上可見一斑。據《紐約時報》2018年11月的總結,中共在各國修建了或者正在修建四十多條管道和其它油氣基礎設施,二百多座(條)橋樑、公路和鐵路;近200座用核電、天然氣、煤炭和可再生能源發電的發電廠,以及一系列大型水電大壩。中共在112個國家有投資項目,大多數屬於「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計劃。如果畫在一張地圖上,密密麻麻都是中共投資的項目。中共的觸角已經佈滿了全球。[6]
隨著「一帶一路」逐漸成形,中共的目的和野心也在不斷擴大。通過「一帶一路」,中共企圖打造出一個自己的經濟圈和勢力範圍來抗衡甚至取代美國:貨幣用人民幣,信用依賴中共的支付系統,通信採用中國鋪設的網絡和製造的手機(包括5G技術),交通用的是中國高鐵,建立起一套以「中國製造」為核心的獨立於目前西方標準的中共標準。
(2)「一帶一路」的全球擴張
「一帶一路」初始時期,以中國周邊國家為對象,最遠也就到歐洲,不過很快就超越了這個範圍,把非洲、拉丁美洲甚至北冰洋都包括進去,擴張到了全世界。海上絲綢之路本來是兩條,後來增加了第三條──經北冰洋連接歐洲的北極航道,號稱「冰上絲綢之路」。在非洲和拉美,中共早就有廣泛的經濟活動,現在也都統一到「一帶一路」的主體框架裏,以更大的力度、更快的速度在非洲和拉美進行經濟甚至軍事佈局。
中共「一帶一路」最直接的動因是出口過剩產能,就是把「鐵公基」(鐵路、公路等基本建設)戰略從國內推向國外。沿線國家有很多資源、能源,中共幫助其修建鐵路、公路能夠一箭雙鵰,一是為產品更快更便宜地出口到歐洲打開一條陸地通道,二是獲取必要的資源和能源。因為前提不過是為「世界工廠」擴大出口,所以中共並不是想在「一帶一路」國家扶持製造業,把中國的製造業拱手轉移到這些國家。中共真正的野心是以經濟為先導,逐漸控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命脈,把它們變成中共的勢力範圍甚至是殖民地,成為中共全球佈局上的棋子。作為副產品,「一帶一路」向周邊國家輸出腐敗、債務、邪惡和專制,把共產主義病毒擴散至全球。所以,「一帶一路」從根子上就是一個陷阱和騙局,不會給當地國家帶來可持續的經濟發展。
有很多國家開始警覺,對「一帶一路」項目叫停或者重新審視;中共自己也不得不表示,要針對外界指責的債務陷阱問題做出修正並增加透明度。但是,中共不惜一切代價實現其野心的決心不可小覷。對西方企業來說,在一個動盪的國家裏也許不會有長期的作為,而中共盤算的不是幾年的計劃,而是上百年的計劃。它可以不計成本,在一個動盪的地方長期經營下去。它要的就是培養親共的政府、可以在聯合國為它站台的幫兇。中共要做「亞非拉」的盟主、要對抗自由世界繼而取代美國的野心,使它可以不計自己百姓的死活。西方的私人企業承受不起的代價,中共可以很輕鬆地讓十幾億中國人民勒緊褲腰帶就扛過去了。在這場世界霸權的爭奪戰中,不是中共本身多麼「厲害」,而是中共以十幾億中國人民為人質,用犧牲中國人民來扛起任何代價。
曾任白宮首席策略師的班農對「一帶一路」戰略有個獨特的解讀。他認為「一帶一路」的大膽之處,就是將麥金德—馬漢—斯皮克曼(Mackinder-Mahan-Spykman)三種關於如何統治世界的地緣政治理論整合在一起,組成了一個完整的計劃。[7]英國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麥金德(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提出誰控制了中心地帶(中亞)就控制了世界島(歐亞);誰控制了世界島,就能控制世界。美國海軍歷史學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提出控制海權的戰略:誰控制了維護全球貿易的海道、要塞和運河就能控制世界。而耶魯大學教授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則認為,環繞亞洲的海岸線比中心地帶(中亞)更為重要,誰控制了海岸線就能控制歐亞;誰控制了歐亞就能控制整個世界。班農的觀點反映出西方對中共「一帶一路」和中共野心的警惕。
其實,中共的野心遠遠不止於此。「一帶一路」也並非僅僅以佔領陸權、海權或者要塞港口為著眼點,它根本就是無孔不入地滿世界去鑽空子。亞、非、拉許多從殖民宗主國獨立出來的國家,出現了權力真空,自然就成了中共的目標;蘇聯解體後獨立出來的國家,削弱了宗主國的控制,也成了中共的目標;一些因為動盪戰亂和衝突而讓西方企業望而卻步的國家和地區,中共也是悉數囊括;小國、島國、經濟落後國家、具有戰略利用價值的國家等等,都是中共眼裏的佳餚;就算是在西方傳統版圖中的國家,因為經濟不景氣,債務纏身,也都成為了中共的俎上之肉。從地緣政治上講,中共就是不知不覺把美國包圍起來,用經濟利益來控制當地國家,把美國慢慢地從這些國家中邊緣化,最終剝離出去,從而建立起一個不同於現行國際秩序的、以中共的核心價值觀為基礎的世界新秩序。這種手法,儼然與中共的老伎倆「農村包圍城市」一樣,最後是要取代美國,服務於中共的全球野心。
2)「大周邊外交」戰略圈──把美國擠出亞太
甚麼是中共的大周邊戰略?按照中共智囊的定義:「中國有14個陸上鄰國、6個海上相望國家;再延伸出去,東面是亞太,西面是整個歐亞大陸。也就是說,中國周邊的輻射面佔了世界政治、經濟、安全的三分之二以上。因此周邊外交的佈局不只是一個地區戰略,更不僅僅是一個周邊戰略,而是一個真正的大戰略。」[8]
(1)澳洲是西方薄弱環節
2017年6月,費爾法克斯媒體和澳洲廣播公司發佈了為期五個月的聯合調查,以紀錄片《權力與影響:中國共產黨如何滲透澳洲》披露中共在澳洲滲透、控制活動之猖獗,引起全世界關注。[9]六個月後,澳洲工黨議員Sam Dastyari宣佈辭去參議員一職,因其被曝出收受中共紅色商人金錢,繼而就南海問題發表有利於中共但與其政黨乃至政府立場相左的言論。[10]2016年9月澳洲媒體SBS曾刊登文章,披露一個中國富商在澳洲提供政治捐獻,直接影響澳洲對華商貿政策。[11]不僅如此,中共媒體機構近年來還與澳洲媒體簽了協定,同意澳洲媒體分銷中共媒體的內容。[12]
實際上,早在2015年,澳洲就把達爾文港租給一家與中共軍隊有聯繫的中國公司,租期99年。達爾文港是澳洲防衛來自北方的攻擊的最重要的軍事要塞。當時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表示,這令人感到「震驚」,這個舉動令美國感到措手不及。[13]
2017年,澳洲學者Clive Hamilton撰寫的《沉默的入侵:中國對澳洲的影響》(Silent Invasion: China's Influence in Australia)完稿,但是一連有三家澳洲出版商拒絕出版,因為他們怕得罪中共。最後第三家出版商重新考慮出版,此書才得以面世。此事更令澳洲人擔心中共對澳洲的影響和操控。[14]
更多的人想知道,中共為何如此看重澳洲?中共在澳洲的操控和滲透在其戰略遠景中起何種作用?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於2017年12月初發表的報告《銳實力:正在上升的威權主義的影響力》(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指出,中國(共)以利誘和滲透影響和改變澳洲政界與學術界,一個主要目的是削弱美—澳聯盟。[15]
「在整個澳洲二戰後的歷史中,美國一直是我們地區的主導力量。今天,中國(共)正在挑戰美國的地位。」2017年發佈的澳洲外交政策白皮書如是說。[16]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的國防分析師Caitlyn Gribbin指出,北京試圖在澳洲地區獲得戰略優勢,其目標是「最終結束(美澳)聯盟」。[17]
澳洲是中共最早拓展海外軟實力的試驗地。[18]作為大周邊戰略的重要一步棋,中共對澳洲的滲透可以追溯到2005年。當時外交部副部長周文重抵達坎培拉,向中共大使館的高級官員傳達中央的新戰略。他說,將澳洲納入其大周邊地區的第一個目標是確保澳洲成為中共未來二十年經濟持續增長的可靠和穩定的資源供應基地。長期目標是撬開美澳聯盟。與會者的任務是弄清楚中共如何能夠最有效地實現所謂「在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對澳洲的綜合照響力」。[19]
中共利用經濟手段迫使澳洲在包括軍事和人權的一系列問題上做出讓步。用經濟利益培養密切的人際關係,同時加上懲罰的威脅,是中共迫使人就範的標準運作方式。北京希望將澳洲變成「第二個法國」,一個敢於對美國說「不」的西方國家。[20]
Clive Hamilton在多年詳細調查之後發現,「澳洲的機構──從我們的學校,大學和專業協會到我們的媒體;從採礦、農業和旅遊等行業到港口和電網等戰略資產;從我們的地方議會和州政府,到我們在坎培拉的政黨──正在被中共監管的一個複雜的控制體系所滲透和改造。」[21]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澳洲實際上自願把自己作為中共的資源供應基地,認為中共把澳洲的經濟從危機中拯救出來。Hamilton指出,中共的滲透和影響之所以在澳洲有效,是因為澳洲人「一直允許它在我們的鼻子底下發生,因為我們被只有中國能夠保證我們的經濟繁榮的信念所迷住,以及我們不敢站起來抵抗北京的欺淩」。[22]
大多數善良的西方人最初即使意識到中共在西方社會的滲透和影響,特別是對海外華人社區的滲透和控制,也只是天真地認為,中共各種策略的主要目標是「消極的(negative)」──為了消除持不同政見者和批評者的聲音。但Hamilton指出,這個「消極」目標背後,同時有一個「積極的」野心──利用僑民改變澳洲社會的形式,使西方人都同情中共,讓北京輕鬆控制。然後,澳洲將協助中共成為亞洲乃至世界的霸權。[23]
類似地,中共的滲透和控制同樣延伸至大洋洲的另一個國家紐西蘭,這裏僅舉數例說明。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中國問題專家Anne-Marie Brady教授2017年9月發佈報告《魔法武器》(Magic Weapons),以紐西蘭為例詳述中共如何在海外影響滲透,發揮政治影響力。其中披露的內容包括數名紐西蘭國會現任華裔議員與中共聯繫密切,以及來自中國的紅色富商、華商協會等統戰組織的巨額政治獻金等。[24]Brady教授發佈有關中國在紐西蘭影響滲透的報告後不久,她的大學辦公室遭入室盜竊。失竊前,她還收到一封匿名警告信,信中詳細列出了對那些沒有按照北京官方路線走的人所進行的報復措施,並警告她說:「你就是下一個。」[25]
中國還積極拉攏紐西蘭本土政客:比如以極高的禮遇接待訪華的紐西蘭各政黨要員,高薪聘請很多紐西蘭前政客在中資機構裏擔任要職,或通過其它方式對他們進行利益輸送,以讓他們聽命於中共。[26]
(2)中共覬覦太平洋島國之戰略價值
太平洋海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價值,每一個島嶼都可能成為重要的海上據點。太平洋島國「島小海大」,陸域總面積僅53萬平方公里,海洋專屬經濟區面積卻高達1900萬平方公里,是中國海洋專屬經濟區面積的6倍還多。中共明確表示,和太平洋島國發展關係是其戰略決策。然而,目前這片海域仍屬美國、日本、紐西蘭、澳洲、法國等國的勢力範圍,中共欲在太平洋上發展海軍,拉攏太平洋島國將是首要任務,繼之才能讓這些島國倒向中共,排除美國勢力。[27]紐西蘭教授John Henderson和澳洲教授Benjamin Reilly指出,中共在南太平洋地區的長期目標,就是要取代美國成為此地區的霸權。[28]中共在美拉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和波利尼西亞等群島注入了大筆投資,援建重要的基礎設施項目,鼓勵大量遊客到訪以及開放電子商務平台,其動作規模遠遠超過美國。澳洲作家Ben Bohane警告,美國正在把太平洋輸給中共。[29]
在中共大規模援助、投資這些島國之後,中共官員表現出的狂妄言行,折射出當中共壯大、自我感覺良好時的真實心態:像對待其極權治下的中國人一樣對待其它國家,讓其它國家都臣服於中共才是其目的。指望中共遵守國際準則顯然是不可能的。
2018年在巴布亞新畿內亞召開的APEC峰會上,中共官員一系列令人震驚的粗魯野蠻行為是其野心的一次大曝光,這些行為包括:1)在東道國橫蠻阻止記者(包括東道國記者)採訪習近平與太平洋國家領導人舉辦的一個論壇,要求所有國家的記者報道時採用新華社的通稿。2)為了阻止會議聯合公報中寫入譴責中共不公平的貿易行為的措辭,中共官員霸道地要求會見東道國外長,但後者認為私下會見中方官員會影響其中立性,因此拒絕了他們的要求。誰知此後四名中共官員竟企圖強行闖入外長的辦公室,最終因被警察逐出而未能得逞。3)在會議中,當中共官員認為其它國家「陰謀」針對中共,就在會場裏大吼大叫。中共在這次峰會上的種種惡行,被一位美國高級官員稱為「發脾氣外交」。[30]
(3)中亞五國:用債務陷阱掌控和掠奪資源
隨著蘇聯的解體,中共開始努力建立並加強與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以及烏茲別克斯坦等中亞國家的關係。中國在中亞地區的戰略目標涵蓋幾個層面:首先,該地區是中共在陸地向西擴展的必經之地,並且中共在為貨物進出中國的運輸鋪設基礎設施的同時,可以進一步擴展在中亞地區的商業利益;其次是在該地區攫取自然資源,其中包括煤、石油、天然氣和貴金屬;第三,中亞國家在地緣和文化上靠近新疆,對該地區的控制,可以強化對新疆少數民族的控制。
雖然中共未明說要主宰中亞,但事實上,中共如今已經成為該地區最有影響力的角色。總部設在布魯塞爾的智囊「國際危機小組」(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2013年公佈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共在中亞的動盪不安中,快速成長為該地區佔主導地位的經濟角色。北京把中亞視為原材料和能源基地,以及其低廉消費品的市場。中共也向中亞注入數億美元的援助及投資,名義上是要促進新疆自治區的穩定。[31]
如今,一個巨大的公路、鐵路、空運、通信和油氣管道網絡已經將中國與中亞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中國道路與橋樑公司(CRBC)及其它承包商,已經擔負了該地區高速公路、鐵路和電力傳輸的建設,在世界最險惡的一些地形上鋪路,並為運送中國商品到歐洲、中東和巴基斯坦及伊朗港口而建設新道路。從1992年中國與中亞五國建立外交關係到2012年的二十年間,中國與該地區的貿易總額已增加了100倍。[32]
中共在中亞地區倡導以國家為主導、信貸推動的基礎設施項目重大投資計劃。有學者推測它可能成為一種新的國際秩序的基礎,中國將在這種秩序中發揮主導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中亞是中國外交政策新思想的試驗場。[33]
目前,北京傾向於支持該地區腐敗的獨裁者,且其不透明的投資計劃被認為只對一小部份精英有益。「國際危機小組」的報告指:「每個中亞政權都脆弱、腐敗,並為社會經濟問題所困擾。」[34]北京推動的大規模基礎建設不但和鉅額貸款掛鉤,而且都涉及有利可圖的許可與審批,在威權體制中不可避免地助長腐敗。
以烏茲別克斯坦為例,該國1991年獨立之後就一直由原烏茲別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卡里莫夫掌權任總統,至其2016年去世前,威權統治長達四分之一世紀之久。2005年在東部城市安集延(Andijan)的鎮壓造成數百人死亡。中共則宣佈自己是卡里莫夫的堅定支持者,「一如既往地支持烏茲別克斯坦及本地區各國為維護國家和地區安全與穩定所做的努力。」[35]
中亞國家自身脆弱的經濟結構,加上向中共大筆舉債進行基礎建設,導致這些國家被債務陷阱套住。土庫曼斯坦面臨慘重的經濟危機,通脹率達300%、失業率飆升至50%、商品短缺,同時腐敗叢生。這個中亞威權政府70%的收入來自天然氣出口,而北京目前為其天然氣的唯一買家。[36]北京同時也是其90億美元鉅額外債(佔2018年GDP的30%)的最大債權人。[37]土庫曼斯坦可能不得不將天然氣田交給中國以償還債務。[38]不誇張地說,該國經濟命脈已掌控在中共手中。
在塔吉克,因向中共貸款興建發電廠致使其欠下3億美元債務而無力償還,該國已將一座金礦開採權交給中共抵債。[39]
吉爾吉斯斯坦經濟也岌岌可危。大規模基礎建設造成吉爾吉斯欠北京大筆債務。吉爾吉斯很可能會將其部份自然資源轉讓給後者抵債。該國還和華為與中興合作建設數字通訊設施,加強政府監控,這同時也為中共留下方便的後門。[40]
北京利用蘇聯解體後留下的權力真空,進入哈薩克能源領域。哈薩克的整個經濟基於生產原油,以美元出售,並用這些美元購買廉價的中國產品。除採掘業外,這個國家工業基礎薄弱。大量中國廉價商品湧入,使得本來不堪一擊的哈薩克的原有工業徹底下跪。[41]
中共在中亞地區擴張的另一個動機,是藉此加強打擊其境內新疆維吾爾族異見人士。中共牽頭的上海合作組織的章程允許疑犯在成員國之間引渡,成員國可以派出他們的人員到其它成員國進行調查。中共藉此將打壓維吾爾人的行動擴展到境外,跨國將境外流亡的異議維吾爾人抓捕回來。[42]
(4)打造支點國家,不顧道德搶佔資源
中共的大周邊戰略實施過程中採用了優先打造「支點國家」(pivotal states),然後以點帶面,達到整個區域的戰略目標。所謂支點國家,按照中共智囊的說法,是具備一定實力、中共有能力和資源來引導其行為、在戰略利益上和中共不存在直接衝突、與美國沒有緊密利益關係的國家。[43]除了上述的澳洲、哈薩克等之外,這樣的支點國家還有中東的伊朗、南亞的緬甸等等。
中共在中東最大的投資國是伊朗。伊朗是中東的重要產油國,同時在價值觀上又一直反對西方。於是伊朗自然就成了中共經濟和軍事的戰略合作對象。中共自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和伊朗保持經濟和軍事交往。1991年,國際原子能機構發現中共出口鈾到伊朗,又發現了中共與伊朗於1990年簽訂的秘密核協議。[44]2002年,伊朗的濃縮鈾項目被發現,西方國家的石油公司紛紛撤離,這給中共留下在伊朗乘虛大規模發展的機會。[45]中共與伊朗的雙邊貿易額自1992年到2011年之間呈指數增長,十七年間竄升一百多倍。[46](其後因國際制裁壓力有所放緩。)被國際社會孤立的伊朗如今最大的經濟夥伴是中共。伊朗在中共的幫助下發展了從短程到中程的戰術彈道導彈和反艦巡航導彈,以及水雷和快速攻擊艇。中共甚至幫助伊朗秘密建立了化學武器項目。[47]
另一個受到中共青睞的支點國家是其南亞的鄰邦緬甸。緬甸有漫長的海岸線,能提供一個通往印度洋的戰略性出口。中共把開闢中緬通道視為規避馬六甲海峽風險的戰略步驟之一。[48]緬甸軍政府的惡劣人權記錄一直使其受國際社會孤立。緬甸的1988年民主運動以軍隊鎮壓收場。第二年,北京的坦克也在天安門廣場大開殺戒。兩個被國際社會同聲譴責的極權政府同病相憐,從此開始密切往來。1989年10月,緬甸的丹瑞大將訪問中國,雙方達成高達14億美元的軍火交易。[49]上世紀90年代雙方又有多次軍火交易,中方售緬裝備包括戰機、巡邏艦、坦克及裝甲運兵車、防空炮、火箭等等。[50]中共的軍事、政治和經濟支持成了苟延殘喘的緬甸軍政府的生命線。[51]2013年,投資50億美元、被稱為中國第四大油氣進口戰略通道的中緬油氣管道建成,雖遭當地反對,在中共干預和談判後於2017年投入運行。[52]類似的大型投資還包括密松水電站(目前因當地反對而遭擱置)、萊比塘銅礦。2017年中緬兩國雙邊貿易總額135.4億美元。中共正計劃建立中緬經濟走廊,其中包括打造一個中方佔股70%、出口印度洋的深水港、[53]緬甸皎漂特區(Kyaukpyu Special Economic Zone)工業園等。[54](接下文)
*****
[1] 趙可金:〈和平發展道路:模式的突破〉,《人民網》,2009年11月11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10355796.html。
[2] 國防大學等:《較量無聲》,2013年6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UjkSJxJDcw&t=2190s。
[3] “Testimony of Arthur Waldron,” in “U.S.-China Relations: Status of Reforms in China,”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April 22, 2004,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WaldronTestimony040422.pdf.
[4] 克里斯‧賈爾斯:〈世行:中國今年或將成全球最大經濟體〉,《金融時報中文網》,2014年4月30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6024?full=y&archive。
[5] 陳良賢,蘇顥雲:〈海外港口熱:中企如何布局?〉,《澎湃新聞》,2017年8月17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58810。
[6] Derek Watkins, K.K. Rebecca Lai and Keith Bradsher, “The World, Built by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8, 2018,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8/11/18/world/asia/world-built-by-china.html.
[7] Andrew Sheng, “A Civilizational Clash with China Comes Closer,” Asia Global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anuary 16, 2018, http://www.asiaglobalinstitute.hku.hk/en/civilizational-clash-china-comes-closer/.
[8] 吳心伯:〈對周邊外交研究的一些思考〉,《世界知識》,2015年第2期,http://www.cas.fudan.edu.cn/picture/2328.pdf。
[9]“Power and Influence: The Hard Edge of China’s Soft Power,”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June 5, 2017, https://www.abc.net.au/4corners/power-and-influence-promo/8579844.
[10] “Sam Dastyari Resignation: How We Got Here,”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December 11, 2017, https://www.abc.net.au/news/2017-12-12/sam-dastyari-resignation-how-did-we-get-here/9249380.
[11] 〈深度:中國捐贈對澳洲影響有多大?外國政治獻金是否該禁?〉, SBS News, September 12, 2016, https://www.sbs.com.au/yourlanguage/mandarin/zh-hant/article/2016/09/12/shen-du-zhong-guo-juan-zeng-dui-ao-zhou-ying-xiang-you-duo-da-wai-guo-zheng-zhi?language=zh-hant.
[12] Mareike Ohlberg and Bertram Lang, “How to Counter China’s Global Propaganda Offensive,”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1,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9/22/opinion/how-to-counter-chinas-global-propaganda-offensive.html?_ga=2.63090735.1831033231.1544154630-97544283.1541907311.
[13] Jonathan Pearlman, “US Alarm over Aussie Port Deal with China Firm,” The Strait Times, November 19, 2015,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australianz/us-alarm-over-aussie-port-deal-with-china-firm.
[14] Tara Francis Chan, “Rejected Three Times Due to Fear of Beijing, Controversial Book on China’s Secret Influence Will Finally Be Published,” Business Insider, February 5, 2018,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australian-book-on-chinas-influence-gets-publisher-2018-2.
[15] Christopher Walker and Jessica Ludwig, “From ‘Soft Power’ to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in the Democratic World,” in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2017), 20, https://www.ned.org/wp-content/uploads/2017/12/Sharp-Power-Rising-Authoritarian-Influence-Full-Report.pdf.
[16] 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7, https://www.fpwhitepaper.gov.au/foreign-policy-white-paper/overview.
[17] Caitlyn Gribbin, “Malcolm Turnbull Declares He Will ‘Stand Up’ for Australia in Response to China’s Criticism,”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December 8, 2017, https://www.abc.net.au/news/2017-12-09/malcolm-turnbull-says-he-will-stand-up-for-australia/9243274.
[18] 陳用林:〈陳用林:澳大利亞正在淪為中國的後院〉,《大紀元新聞網》,2016年9月2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6/9/2/n8261061.htm。
[19] Clive Hamilton. Silent Invasion: China’s influence in Australia (Melbourne: Hardie Grant, 2018), Chapter 1.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同上。
[23] Clive Hamilton, Silent Invasion: China’s influence in Australia, Chapter 3.
[24] 林坪:〈揭祕中國銳實力(十)紐西蘭〉,自由亞洲電台,2018年9月25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zhuantixilie/zhongguochujiaoshenxiangshijie/jm-09252018162912.html。
[25] 同上。
[26] 同上。
[27] 林廷輝:〈龍在陌生海域:中國對太平洋島國外交之困境〉,《國際關係學報》,第三十期(2010年7月),頁58。https://diplomacy.nccu.edu.tw/download.php?filename=451_b9915791.pdf&dir=archive&title=File。
[28] John Henderson and Benjamin Reilly, “Dragon in Paradise: China’s Rising Star in Oceania,”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72 (Summer 2003): 94-105.
[29] Ben Bohane, “The U.S. Is Losing the Pacific to Chi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7, 2017,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u-s-is-losing-the-pacific-to-china-1496853380.
[30] Josh Rogin, “Inside China’s ‘Tantrum Diplomacy’ at APEC,”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0,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josh-rogin/wp/2018/11/20/inside-chinas-tantrum-diplomacy-at-apec/.
[31] “China’s Central Asia Problem,” Asia Report No.244 (Brussel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Feb 27, 2013), https://www.crisisgroup.org/europe-central-asia/central-asia/china-s-central-asia-problem.
[32] Wu Jiao and Zhang Yunbi, “Xi Proposes a ‘New Silk Road’ with Central Asia,” China Daily, September 8, 2013, http://www.chinadaily.com.cn/sunday/2013-09/08/content_16952160.htm.
[33] Raffaello Pantucci, Sarah Lain, “China’s Eurasian Pivot: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Whitehall Papers 88, no. 1 (May 16, 2017),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2681307.2016.1274603.
[34] “China’s Central Asia Problem,”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https://www.crisisgroup.org/europe-central-asia/central-asia/china-s-central-asia-problem.
[35] 〈孔泉:中國支持烏茲別克斯坦為國家安全所做努力〉,人民網,2005年5月17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8212/14450/46162/3395401.html。
[36] Benno Zogg, “Turkmenistan Reaches Its Limits with Economic and Security Challenges,” The Global Observatory, July 31, 2018, https://theglobalobservatory.org/2018/07/turkmenistan-limits-economic-security-challenges/.
[37] Jakub Jakóbowski and Mariusz Marszewski, “Crisis in Turkmenistan. A test for China’s Policy in the Region,” Centre for Eastern Studies (OSW), August 31, 2018,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osw-commentary/2018-08-31/crisis-turkmenistan-a-test-chinas-policy-region-0.
[38] Eiji Furukawa, “Belt and Road Debt Trap Spreads to Central Asia,” Nikkei Asian Review, August 29, 2018,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Belt-and-Road/Belt-and-Road-debt-trap-spreads-to-Central-Asia.
[39] “Tajikistan: Chinese Company Gets Gold Mine in Return for Power Plant,” Eurasianet, April 11, 2018, https://eurasianet.org/tajikistan-chinese-company-gets-gold-mine-in-return-for-power-plant.
[40] “Risky Business: A Case Study of PRC Investment in Tajikistan and Kyrgyzstan, ” China Brief (Jamestown) 18, no. 14,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risky-business-a-case-study-of-prc-investment-in-tajikistan-and-kyrgyzstan/.
[41] Juan Pablo Cardenal, Heriberto Araujo, China’s Silent Army: The Pioneers, Traders, Fixers and Workers Who Are Remaking the World in Beijing’s Image (New York: Crown Publishing Group, 2013), Chapter 2.
[42] Lindsey Kennedy & Nathan Paul Southern, “China Created a New Terrorist Threat by Repressing Secessionist Fervor in Its Western Frontier,” Quartz, May 31, 2017, https://qz.com/993601/china-uyghur-terrorism/.
[43] 徐進等:〈打造中國周邊安全的「戰略支點」國家〉,《世界知識》,2014年15期,頁14-23,http://cssn.cn/jjx/xk/jjx_lljjx/sjjjygjjjx/201411/W020141128513034121053.pdf。
[44] Therese Delpech, Iran and the Bomb: The Abd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49.
[45] Juan Pablo Cardenal, Heriberto Araujo, China’s Silent Army: The Pioneers, Traders, Fixers and Workers Who Are Remaking the World in Beijing’s Image, Epilogue.
[46] Seyed Reza Miraskari, et. al., “An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in Iran-China Trade Relations,” Journal of Money and Economy 8, No 1 (Winter 2013): 110-139, http://jme.mbri.ac.ir/article-1-86-en.pdf.
[47] Scott Harold, Alireza Nader, China and Iran: Economic, Political, and Military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RAND Corporation, 2012), 7,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occasional_papers/2012/RAND_OP351.pdf.
[48] 〈繞過「馬六甲困局」的商業基礎——如何保證中緬油氣管道有效運營〉,《第一財經日報》,2013年7月22日,https://www.yicai.com/news/2877768.html.
[49] Li Chenyang, “China-Myanmar Relations since 1988,” in Harmony and Development: Asean-China Relations, eds. Lim Tin Seng and Lai Hongyi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2007), 54.
[50] 同上。
[51] “China’s Myanmar Dilema,” Asia Report No.177 (Brussel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 2009), 1, https://d2071andvip0wj.cloudfront.net/177-china-s-myanmar-dilemma.pdf.
[52] 〈閒置兩年後 中緬原油管道終於開通〉,《BBC中文網》,2017年4月10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39559135。
[53] 莊北甯,車宏亮:〈中緬簽署皎漂深水港專案框架協定〉,《新華網》,2018年11月8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8-11/08/c_1123686146.htm。
[54] 鹿鋮:〈中緬經濟走廊:緬甸發展的新興途徑〉,《光明網》,2018年9月17日,http://news.gmw.cn/2018-09/17/content_31210352.htm。
------------------
📰支持大紀元,購買日報:
https://www.epochtimeshk.org/stores
📊InfoG:
https://bit.ly/EpochTimesHK_InfoG
✒️名家專欄:
https://bit.ly/EpochTimesHK_Colu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