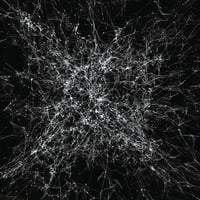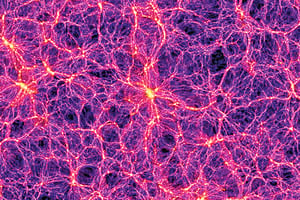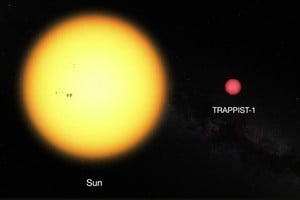他躺在冰櫃裏已經10年了,死的時候是42歲。 2008年2月6日,他因「奧運安保」被抓進看守所,8天後死亡。他年邁的老母親至今都以為他還活著。他是一個樂手,畢業於北京大學。在公開場合,他的名字不再被他的樂隊提及,換了樂手的樂隊,目前仍活躍在大陸樂壇。他的很多朋友、同學不能公開紀念他,對他的死諱莫如深。他的名字被中國官方網站屏蔽,他叫于宙。
(接上期)
他總是不合時宜,他的同學說,我們不懂他。他不愛說話,心裏有主意,不太和人說心裏的想法。
折騰了兩年,于宙最後否定了他所有的搖滾作品,他認為音樂「不應該是宣洩」,而且,搖滾圈裏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兒也讓他越來越疏離,他說,「我心中是有淨土的」。
1997年于宙接觸了法輪功,剛開始就發生了奇蹟。當時他腰間盤突出,連幾斤重的米都拎不了,看《轉法輪》不到一個月,他就能背一個人上六樓了。但這還不是他要修煉的根本原因。
他興奮地告訴朋友:「我有師父了!我知道生命的意義了……」
不是所有人都關心這個。他笨嘴拙舌,說話又慢,被搶白一通後,也就默默地給侃侃而談的朋友們端茶倒水了。他不氣惱,也不辯解。他的真誠和孩子氣,讓習慣了插科打諢的朋友們也不忍心嘲笑他。
在一個小本上,他工工整整寫了這句話:你是否正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對人好。
還有一句歌詞後來被發現:
當我發現自己不屬於這個世界
我決定與它和平共處
他寫字一筆一畫的,他學不會連筆字,瀟灑不起來,以至後來在CD上給粉絲簽名,也笨拙得很。
「師父把我從地獄裏撈出來,洗乾淨」,有一天夜裏打坐後,于宙說:「真正的覺者,是能為真理而赴湯蹈火的。」那是1999年初,于宙妻子回憶,當時他表情肅然,像小學生一樣,手放在自己的心口。
1999年7月20日,法輪功被中共定為「×教」後,全國各地有大量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上訪。很多外地學員在于宙家有過短暫的停留。于宙帶回了搞電腦的黃雄來家裏交流,吉林大學數學系教師沈建利和她二歲的女兒格格、工程師雲慶彬夫婦和他們的小兒子、大連輕工學院的陳家福等等,都在他家住過。武漢的彭敏那時也偶爾到他家洗個澡,晚上彭敏在菜市場的攤位上睡覺。
于宙有時開車把學員送到天安門,然後到樂隊排練。晚上演出後,有時會往家拉違禁的書和資料。有一次,他裝了一後車箱的《法輪功》,到家後說:「我害怕,總感覺警車在後面嗚嗚跟著。」但下一次讓他去拉書,他還是毫不猶豫。
那時他家最多一次住過五、六十人。警察來了,抄家。人不斷被抓走,被拘留、被判刑、被勞教。于宙也被拘留了兩次。
2001年4月,彭敏死了,22天後,彭敏的母親也死在同一家醫院。看到消息後,于宙異常嚴肅,對妻子說:「將來我們兩個不管是誰,如果是因為修煉而死,另外一個人一定不要難受。」
不久妻子被判刑5年,罪名是「利用邪教組織迫害法律實施」,那次如果不是于宙出去排練,也會一同被堵在家裏的。
于宙對監獄警察直言自己也修煉,所以就幾乎得不到探視妻子的權利。唯一有一次電話接見,隔著玻璃,他拿著話筒對妻子說:「你過得比我更有意義。」那5年于宙與樂隊一起,繼續排練演出。
一位粉絲朋友後來接受採訪時回憶:「我一直不知道于宙家裏的事。但那天他特別高興,說第二天他妻子就要回家了,說她在監獄已經整整5年了。接著于宙就談了他們的信仰,而且他說了一句話,後來我才反應過來,當時我以為他不過就是說說罷了。他說:『我是能為信仰付出生命的。』」
那時樂隊已經有了名氣,評論說,他們樂隊用音樂搭建了一個世外桃源,閉上眼睛聽他們的音樂,好像就進入了林中山谷,就可以遠離世俗的煩惱。樂隊名字叫「山谷裏的居民」。
2007年11月16號,樂隊在中國傳媒大學開始了巡演的第一站。最後的壓軸曲目是于宙唱的。他自己吹口琴伴奏,翻唱了羅大佑的《愛的箴言》:
我將生命付給了你
將孤獨留給我自己
我將春天付給了你
將冬天留給我自己
…………
他神情漠然,沒有一絲煽情,也沒有與台下互動。一個在場的學生說,傳媒大學的舞台,一般人鎮不住,最後一曲都會被習慣性惡搞,多大的腕兒都會被哄台。很奇怪,那天台下的學生居然沒人起哄,也不知于宙怎麼就鎮住了場。
兩個多月後的一個晚上,于宙與妻子開車回家,路上被警察攔截。他們的身份證號碼被當場聯網查驗,很快證實他倆均修煉法輪功。警察在于宙的吉他袋裏找到了幾張神韻光盤。那一夜,他們作為「同案」被扣在派出所訊問。那是中共「創建平安奧運」的第一天——2008年1月25日。
他妻子回憶:
「第二天我們被拉到醫院體檢,之後在通州看守所門口再次體檢,體檢合格才可以被拘留。在羈押室門口,走在前面的于宙突然就停住了,轉過身對我說:『這一次,我將以生命為代價。』他表情僵硬,看著我,又說:『你放心,我行。』
「進了羈押室,他甚麼都不配合,我聽見他對警察說:『我沒有罪』,警察對他吼起來……那幾天南方爆發了特大雪災,北京也奇冷無比。」
8天後,于宙的在京家屬被通知「于宙病危」,他們趕到北京999急救中心,但不許接近于宙的身體,周圍擠滿了黑衣警察。當晚22點,于宙被宣佈死亡,警察稱死於糖尿病。
那是除夕之夜,北京城的鞭炮不停歇地炸響,讓人心慌。于宙姐姐說:從那以後,我再聽不了鞭炮聲了。後來于宙在她的夢中出現,對她說,「姐,不要難受,死,只不過是在世間脫下了一件衣服。」
隔著看守所的柵欄門,警察對許那宣佈了于宙的死訊,她沒有掉一滴眼淚。第一次被判刑時,她的「同案」、法輪功學員李麗死在看守所,這次的「同案」是她丈夫,又死在看守所。她想起了丈夫曾對她說的那句話:將來我們兩個不管是誰,如果是因為修煉而死,另外一個人一定不要難受。
許那就于宙的非正常死亡向通州看守所提出了控告,因其是法輪功修煉者,檢察院「不予受理」。 之後她再次被判刑3年。
于宙的姐姐要求警方出示當時的監所錄像,警方開始說,「可以給你看一部份」,後來又說,「錄像都刪了」。
「于宙被拉到醫院前,每天我都和他在一起。」一個與于宙同監室的在押人2011年出現了,他聲稱見證了于宙在看守所最後的日子。
「他受的苦不是人受的」,他豎起大拇指,「于宙是一個爺們!沒見過這麼剛兒的爺們!」這個不願公開姓名的人還說,「通州看守所草菅人命,責任警察叫董亞生,會武術。」百度網上查到,董亞生曾被評為全國優秀警察,是警察系統內的武術冠軍。
他不想死,但他決絕做出了一個決定:「我將以生命為代價。」
在此之前,他認識的一些修煉者有罹難的,包括沈建利,還有黃雄失蹤15年都沒有消息,陳家福和彭敏被打死,參與長春插播的雲慶彬被逼瘋,他的妻子,也因為不認罪遭受酷刑。他當然非常清楚,他的選擇可能是「要拿命去換的」。
他的北大同學說,于宙生活的每一步都出人意料,但他的死,確實很難接受,因為「他不是叛逆的人,也不偏激,他性格忍隱,甚至很柔弱,不會與任何人為敵」。
他只是堅持:「我沒有罪」,他只不過單純地把自己的思考和生命實踐融貫在一起,試圖以肉身去承擔這個結果。
當普通人已經無力抵擋國家機器的碾壓,當努力適應環境成為實利教育的目的,當趨利避害地遊刃有餘於現實成為一種智慧,當集體噤聲、選擇性遺忘、顧左右而言成為中國知識份子的常態,作為北大學子,于宙死的一個意義就凸顯出來:一個人僅僅為堅守一個最基本的常識,就可以付出生命的代價,而更多的人,還沒有能力去面對這一最簡單的問題。
于宙死後一直躺在冰櫃裏,他的名字被中國網站屏蔽,所有與他相關的文字影片幾乎都被刪除。而在一個老式卡帶裏,還能放出他20多年前的哼唱:
我已經活了一百來年
一個無奈的軀殼
一個混亂的空間
是不是在我離開以後
天與地仍然會不停地轉
…………
感謝所有接受採訪的人。(全文完)◇
-------------------
局勢持續演變
與您見證世界格局重塑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