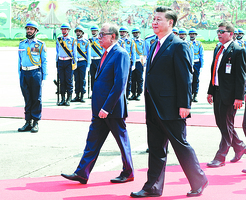我開始寫「羊憶蓉隨筆」(編注:發表於1990年前後),最初的想法,是覺得自己平日政論文字寫多了,關注問題的焦點和文章筆法都有些僵化,很希望換個園地來「隨筆」一下。
一兩個月下來,每每發現有感想和有興趣的題材,仍在政治和社會問題,好像先天受到某種「制約」,侷限了自己的視野。我一面苦惱自己距離「隨心所欲」尚早,一面忽然領悟到,是不是因為走上讀書教書的路,再也脫不開自以為「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枷鎖?
知識分子,不管專精的學科是甚麼,很難避免對政治問題的關心。最近中國大陸的大學生又起風潮,不但聲勢浩大,而且對中共政權批評非常嚴厲,是繼知識分子寫聯名信要求釋放政治犯之後的又一波民主活動。
我們隔岸看得十分振奮,有人順勢表示「同情」,有人跟著也追悼胡耀邦,好像中國的民主前途就寄望於這些批判性強烈的青年知識分子身上了。
但知識分子永遠是這麼勇於向政治現實挑戰嗎?卻又不然。在中國尤其不然。科舉制度為中國讀書人的求知提供了現實出路,好的方面說,讀書人一展抱負,政府廣納人才。但反過來,這種政治利益的交換,何嘗不軟化了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格。
所以,中國知識分子在政治勢力之前,其實是很軟弱的,而且常常不自覺地默認了做官和讀書之間的某種「主從」關係。
有一次我在研究室做功課,門外人聲嘈雜,好像有大隊人馬經過,間歇聽見有人在說「教育部的長官來了」。還有人敲了我研究室的門,很善意地介紹我與「長官」認識寒暄。後來才知道是教育部的督學來視察。
我本來十分感慨,不明白督學視察何以被人前呼後擁,更不明白教育部的公務員於大學教授而言,何「長官」之有。但轉念一想,我們的資格證書,升等審查,校方的預算人事,乃至校長任命,全由教育部做主,教育部不是長官又是甚麼!
這樣一想,應該可以很阿Q地釋懷了,卻是心情更為沉重!
政治權力對知識分子的限制,政治權力對知識分子的引誘,都嚴重傷害了知識分子的批判和獨立性格,也損傷了理想主義的熱情。但很多知識分子的確未察覺這種「致命的吸引力」的陷阱,而以「使命感」包裝了自己的權力欲望。
有人批評「學官兩棲」的狀況,其實在中國傳統,學、官從未異途,根本就是「學官一途」。所以我們今天有高學歷的內閣,其中有些的確可稱為「技術官僚」,但也有人是從曾經年輕熱情、批評力旺盛的學者起家。甚至連同某些具有廣大群眾基礎的民意代表,一起被收服在這龐大的官僚體系之下。
上禮拜「聯副」有大陸留美學生龔小夏的一篇文章,談仍在獄中的王希哲,慨歎為甚麼中國人能容忍世上最荒唐的政府,卻不能容忍單槍匹馬、唐吉訶德式的英雄。如果追問答案,我想,在中國,也許唐吉訶德從來不被讚許是一個英雄吧!
我有一次和一位標準的「從政學人」談話,聽他侃侃談起自己的使命感,間歇也批評了官場的權力傾軋。我忍不往譏諷地說:「學者去做官,有使命感的和有權力欲的很難區別。因為兩者同樣是對外宣稱具有使命感,私底下卻免不了爭取權力。」
我很感激這位「長官」原諒了我對他的不尊敬,但我更難忘的是他當場滿臉驚愕,無法應答的尷尬表情。若問知識分子與政治有甚麼關聯,當時那靜默尷尬的一刻便是某種答案吧!◇
——節錄自《太陽下山明朝依舊爬上來》/ 聯經出版公司
-------------------
局勢持續演變
與您見證世界格局重塑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