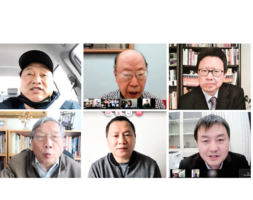1952年,司馬璐在香港出版《鬥爭十八年》,寫出了「中共官方不能言、不敢言的歷史真實故事」,和自己從投奔革命到認清共產黨內部殘酷鬥爭的本質,再到選擇自由的心路歷程,轟動一時。
以中共黨史專家著稱,並被稱為「國共歷史見證人」、「中國政治人物活辭典」的百歲人瑞司馬璐(本名馬義),於美東時間2021年3月28日在紐約Flushing Union Plaza安老院無疾而終,享壽103歲。
司馬璐是江蘇海安人,生於1919年(與「五四」運動同年)黃曆閏七月初五,早在青少年時代,就已投身革命洪流。
司馬璐18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歲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圖書館館長,20歲擔任《新華日報》延安辦事處主任。脫離中共後,司馬璐長期從事黨史研究,被稱為史學專家。
司馬璐的「延安夢」破碎
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共產黨員和左傾人士的心目中,延安是當時的「革命聖地」,能夠去延安打一個轉,就好像出洋鍍過金一樣,即使是一個白癡,他們也得對他敬畏三分。遇到爭論,聽說某人是剛從延安來的,大家也就寂然無聲了。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先生就是他們中的一個。
1937年底,司馬璐受黨組織的派遣,去延安學習。能去到自己心目中的「聖地」,司馬璐可謂如願以償。他在自己的回憶錄裏說,當年「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延安夢』,這個夢有點像著名的童話故事《愛麗斯漫遊奇境記》。」
他回憶初到延安時的情形說:「我有一個『延安夢』,這時又真的身在延安,也就自然入夢,人在夢中不覺是夢。我們黎明起身後就開始迎著寒風劈開冰塊,用人的體溫把冰化成水。我們吃的是小米飯,菜是紅蘿蔔或是南瓜,營養當然是說不上的,每餐如此,甘之如飴。我們把自己的苦行視為革命者應有的情操,因為我們身在夢中。」
但很快,司馬璐就發現,延安並不是他想像中的天堂!他感嘆:「延安每一個青年都會唱《延安頌》,把延安唱得像天堂一樣美好。實際上這個天堂只存在我們夢中。」
奔赴延安的青年,可以說幾乎個個都有自己的理想和期望。司馬璐也不例外。可事實很快就給他上了一課——黨根本就不關注你的理想和期望,只要求你做它的馴服工具。
到了延安以後,司馬璐對黨的組織是如何控制黨員的有了深刻的體會。
他感概道:「史太林說『共產黨人是特種材料做成的』,他自己取名『鋼』,一般的幹部應是木料,有的可做棟樑,有的只可燒火。不同的領導主宰一個黨員不同的命運。黨員除服從之外,絕不可以還價,也無權問為甚麼。」「『組織』對於我們每個人都具有一種神秘的控制力量,有許多生龍活虎似的青年,經過兩次組織生活以後,一個個都像綿羊似的馴服了。」
司馬璐出書揭露中共黑幕
1952年司馬璐在香港出版《鬥爭十八年》,寫出了「中共官方不能言、不敢言的歷史真實故事」,和自己從投奔革命到認清共產黨內部殘酷鬥爭的本質,再到選擇自由的心路歷程,轟動一時。
以下是該書記錄的若干中共黑幕:
杯水主義
延安男女盛行「杯水主義」,青年女性因緊俏(性別比例18︰1)而昂然於群。抗大副校長羅瑞卿死纏司馬璐女友夏森,強行約會,關門不讓走。
夏森在日記中哀嘆:「羅校長啊,你為甚麼一定要糾纏我呢?女人,女人,女人到哪裏都是一樣啊!」
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招待所住著一位孕婦,說不出肚子裏誰是「孩子他爹」,勉強說出辦事處裏兩名男性,人家又都不認帳。
一般女同志被派出工作,除了少數以外,差不多始終只做些男同志的輔助工作,她們多半以「臨時太太」的身份,由黨暫時配給某一個男同志。
這是革命工作呀,她們當然只得服從,她們時而被調開,時而又配給另一個男同志。在這些女同志的工作期間,「臨時太太」造成多少悲劇,女同志們流了多少眼淚,出現了多少辛酸的故事啊!
紅色恐怖
1941年初「皖南事變」後,司馬璐受命自渝赴皖,以屯溪為中心展開皖南浙西的地下活動,頂頭上司是中共閩浙贛三省特派員「老頭子」(司馬璐稱「柳英」,即劉英),他向司馬璐描繪中共紅色恐怖:
「每一個高級的負責同志都提醒我們,不僅要提高對黨外的警惕性,而且要提高對黨內同志的警惕性,他們隨時在相互之間需要『了解』,當然也一樣需要『了解』。……一個愈像忠實可靠積極的同志,愈要當心他。……沒有一個同志是絕對可靠的;為了革命,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
劉英向司馬璐介紹江西清肅AB團:
「今天看著一批同志審判別人,明天又看到那些昨天審判別人的人,又在被另一批同志審判,一批批一批批綁出去殺了。我敢說這中間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冤枉的,但是我也敢保證黨的政策是絕對正確的。」
一位前幾天還在灌劉英辣椒水的幹部,竟也以AB團罪名被處決。
「老頭子」接著論證三種人必須殺:一、接受黨內審查時順竿自誣招供者,這種人意志薄弱,本質易於動搖;二、受冤屈而激怨者,此類人忠誠度不夠,容易成為叛黨分子;三、亂用AB團名義殺人者,這種人「當然黨也是一併殺了」。
由於懷疑一切,你越是忠實積極,越可能遭組織上「關心」,「殺了乾淨」。
屯溪事件
屯溪某布店是中共聯絡站,李老闆夫婦連夥計不過四人,但開飯時總坐滿一桌。不過雖然吃在一張桌上,彼此不通問也不介紹。另一聯絡站為王大嫂處,專門用於個別談話。
王先生據說長年在外跑單幫,其實是中共華東局派來的一對假夫妻,租好房子後,王先生就奉命調往別處,王大嫂就成了「老頭子」的情婦。
一次,司馬璐請王大嫂遞一張條子給「老頭子」,遭到一陣訓斥。司馬璐辯解:「王大嫂是我們自己人。」老頭子歇斯底里暴跳起來:「誰是自己人?誰?誰?」
「老頭子」還告訴司馬璐,「上海平日殺共產黨最起勁的巡捕,說不定就是共產黨員,因為他們不多殺一些共產黨員是沒法取得上面的信任的,多死幾個自己的幹部有甚麼關係,何況這也是對黨的一種貢獻呢。」
一次,幾個聯絡站的安全信號全撤下,原來一位自製炸藥的本地同志失手,發生爆炸,被鄰居當成漢奸扭送警察局。由於此人知道幾處聯絡點,只得全體「緊急搬家」。
三天後,「漢奸」出獄,聽說他家裏花了點錢。「老頭子」判定是國民黨的反間計。幾天後,「漢奸」失蹤。司馬璐問「老頭子」:「是不是我們把他幹了?」最初,「老頭子」推託不知道,後對司馬璐講了一套理論:
「你知道嗎?革命是需要殘酷的,昨天的同志,可能今天就是我們的敵人。……錯殺一個,沒有甚麼了不起,一個人有甚麼關係,革命是多麼一件大事。」
但那位「自製炸藥」同志的家屬卻向地方當局要人,警察局當然不知下落,家屬卻盯著:「先前被你們關過,現在繼之以失蹤,還不是你們幹的嗎?」
此時,「老頭子」布置屯溪中共地下黨員發動地方紳士出面,控訴國府殘殺青年,油印傳單寫得十分淒婉,聲稱這次事件是「國民黨的又一滔天罪行」。而國民黨也把所有憲警訓斥一頓。
「屯溪事件」後不久,「老頭子」再次開導年輕人:當發現一個同志不可靠的時候,最好是能夠通過敵人的手把他幹掉。因為這是一舉兩得的事,既可以為我們組織上除去隱憂,又可以增加我們的政治宣傳資料。否則的話,只好我們自己動手了,不過,那總是不得已的。
「最可怕的是:中共的紀律,像老頭子這樣的負責幹部,被捕後即使不死在國民黨手裏,釋放後組織上也會立刻派人去把他幹掉的。」
勾結日寇
司馬璐發現,「共產黨人所關心的不是抗戰的勝利,而是如何加重這些腐蝕的因素,加速這個社會秩序的破壞,動搖抗戰的基礎,打擊政府的威信,以便於他們準備革命條件。」
「在敵人的偽組織機構中,大量地充斥著我們的同志,他們藉日本人的刀,去屠殺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人員,甚至我們黨的組織也經常與日本人的特務機關交換情報。據我直接知道,上海兩次破獲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和一次江南日本人對忠義救國軍的圍剿,都是我們黨在日本人合作之下的傑作。」
「做漢奸也是革命,聽說好多大漢奸都是我們黨的同志,比如像袁殊(當時的偽中央宣傳部長)」。
籌款秘訣
游擊隊員瞿飛幾年躲在山裏,實在太苦,此時調來做白區工作,負責管錢的財務,「真是到了天堂哪!」幾杯老酒下肚,他向司馬璐透露游擊隊如何解決經費問題:
打土豪是個辦法,可是現在不行了,不過你要是指他是個通敵的漢奸,他就沒有話說了,反正是不必經過公審的。或者還可以把游擊區以外的有錢的紳士拖進來。……武裝走私也是個辦法,伏擊敵人的運輸車輛也是個辦法,不過那總是太危險了。
其實,只要下得了狠心,找錢也不難。最有效的辦法是直接向老百姓搶……
「那不是使老百姓要對我們發生反感嗎?」司馬璐問。
你真是又太書生之見了,這完全是技術問題。比如說,我們先派一部份同志化裝土匪去搶了,等到老百姓報告到我們隊裏來,我們就立刻派一支部隊追上去。
這時,我們那些奉命搶掠的同志,已經滿載而歸,從另一條路歸隊了。這樣,老百姓不但不會對我們有反感,我們地方黨的組織,還要發動老百姓對我們慰勞呢!
這位游擊隊員還向司馬璐透露了另一「萬萬說不得」的籌款途徑——印製假鈔,「你不見我們黨裏拿出來的都是一疊疊的新鈔票嗎?還不是這麼嘩啦嘩啦發出的?!」
對自己「同志」滅口
司馬璐延安棗園「敵工培訓班」同學陳健民,昆明國府後勤機關工作人員,中共地下黨員。
一天,黨命令他逮捕某人並立即處決,事後再向政府公布此人為圖謀不軌的共黨份子。當陳健民遵命將此人逮捕,一看,原來也是棗園同學——會唱山歌的矮個子李毓茲。
經過交談,原來昆明中共組織經費十分困難,李毓茲奉命搶劫昆明大商號源昌公司。事後才知道這家公司有龍三公子股份,龍雲追緝甚力,限期破案。昆明中共地下組織這下慌了神,因為中共在西南的活動全靠龍雲掩護,現在搶了人家公子的公司,一旦破獲,如何得了?
至此,陳健民才明白組織命令他捕殺李毓茲,竟是為了滅口!他把自己「任務」告訴老同學,兩人相擁而泣。最後,陳健民送了一點路費給李毓茲,囑他走得越遠越好。陳健民自己提一隻小箱,悄悄逃至重慶。
正是上述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使司馬璐最終認清了中共的真實面目,在痛苦中覺醒了。
他寫道:「這個黨是一個完全以命令支配黨員行動的黨,軍事化的黨,特務化的黨。每個黨員,毫無保留地毫無還價地服從黨的紀律。黨的基本政策就是「殺人越貨」四個大字。」
「這許多年來。我的一顆純潔的心一天天受到損傷,我貢獻了我的青春給這個理想——我過去把它看得如何的崇高和偉大。如今,它的光芒在我面前已經全部變得漆黑,這個追求,今天已經徹底的幻滅了!」◇
------------------
📰支持大紀元,購買日報:
https://www.epochtimeshk.org/stores
📊InfoG:
https://bit.ly/EpochTimesHK_InfoG
✒️名家專欄:
https://bit.ly/EpochTimesHK_Colu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