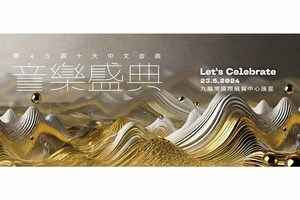「偉大的藝術,也就是古典藝術的主要功能是傳達情感,將個體的內在情感傳達給他人。這種溝通是神聖的——這是個老派的說法了。它顯示著一個生命對另一個生命的敬畏。如果一個人能說『是,我也有這種感受!』他就掌握了尊重每個個體生命神性的一面。通過這種深刻的溝通,我們提供了某種和解——某種『和平契約』,達致世界和平。」
多年來為古典歌唱家擔任鋼琴伴奏的畢格(Raymond Beegle)認為,任何形式的古典藝術都給人以希望。
「流行音樂」——在他看來是古典音樂的對立面。「流行音樂被定義為情感張力和跨度小於古典音樂,且其目的是營利。」他這樣引述道。
「古典藝術給人類帶來希望,因為它們體現著更高的理想。」
他表示,在今天,音樂常被看作以營利為目的,他提到美國作曲家格拉斯(Philip Glass)的話:「我的父親經營一家唱片店,所以我對音樂的最初了解就是:它是一門生意。」
畢格將流行音樂視為一門迎合低下人性的生意。在他看來,我們正陷於貪婪和暴力的可怕困境中,過份看重情慾。流行音樂正是迎合這些、助長這些。
畢格相信,古典藝術給人類帶來希望,因為它們體現著更高的理想、視角和願景,能夠提升我們低劣的本能和慾望,啟悟我們回歸更高貴的自己。
已入古稀之年的畢格是在漫長的音樂生涯中達致這一認識的。他也與一些著名音樂藝術家私交甚篤,畢格表示,雖然這些藝術家以歌唱為生,但他們從事音樂並不是為了賺錢,其事業的意義全然在於真理、人心,以及分享深刻的願景。
貝多芬《莊嚴彌撒曲》中的《降福經》
貝多芬有句名言:「我熱愛真理超過任何其它事物。」其《莊嚴彌撒曲》(Missa solemnis)中的《降福經》(Benedictus,又稱祝福歌)體現了深刻的人生真理;儘管它是天主教禮儀的一部份,但畢格認為,以榮格的心理學觀點來看,基督進入耶路撒冷時所講的一番話,意義超越了事件本身,超越了信仰的門派之別。
「故事,神話,夢,這些來自潛意識的信息往往有更深的邏輯,提示給我們的東西比哲學和科學更多。」畢格說。它們與人類的真理共鳴,且往往躍動著精湛的美。
「貝多芬的《降福經》抓住了耶穌騎著驢子進入耶路撒冷那的那一刻,眾人歡呼迎接,也許也在低語:『有福了,祂以上帝之名來臨了。』」畢格解釋說。
音樂起於低音絃樂,是基督「賦予沉思、溫暖又慈悲」的心靈的寫照,他十分清楚,自己即將被殺害。
華麗的小提琴獨奏倏然啟始,有如聖靈降世,標誌著神來在人間。然後整個樂團以柔和的和弦加入,「好像在說,『是的,這是上帝之子。』」歌詞由合唱團和獨唱演員交替唱出,以「和散那(Hosanna)於至高之天」作結。(註:和散那,天主教漢譯賀三納,是猶太教和基督教用語,原為祈禱詞「上主,求你拯救」,後用作讚頌之語助詞,帶有歡呼、激勵的意義。)
「這一切以一種穩定而起伏的節奏為基調,代表馱負基督受到盛大的迎接、過後又走向等待他的未來的那頭牲口的步履。」
對畢格來說,這首作品向我們展示了人類的理想——希望,以及對和平的愛與渴望。它謳歌了「人類神性的可能」。
像這樣立意崇高的樂曲,他一年只能聽上兩三遍。「對於音樂家或那些感性的人來說,音樂可以讓人短暫的狂喜,之後我們再次回到人世間。」
在這時候,「你的淚水開始湧動。你會感到自己像液體般透明。事物之美讓你如此滿懷感激。」
畢格似乎在說,當我們達致最高的理解時,美和真理是一體,引發一種沉靜而慈悲的感受。
在《莊嚴彌撒曲》的手稿上,貝多芬寫道:「從我的心傳遞給聽者的心。」
偉大音樂的效果
最優秀的古典音樂「向聽眾呈現一種道義的責任」。「它讓你想成為好人,說真話,盡己所能做好眼前的工作。」畢格說。
他認為這些都是讓一個人快樂幸福的事情,「在我二十多歲時,我做事是為尋求幸福,但沒有奏效。幸福不是目標,它是一種效力。」它是道德的結果。
俄羅斯男中音歌唱家霍羅斯托夫斯基(Dmitri Hvorostovsky)接受腦瘤手術後重返舞台的一場音樂會,畢格參加了。他說,歌唱家看起來「有些孱弱,但唱得極好」。
畢格說,霍羅斯托夫斯基的作品一直關乎真理:正與不正、真相與謊言、絕望和希望的較量。
演唱會結束後,觀眾看起來更溫和,似乎成為比步入禮堂時更好的人。「人人都那麼友善地對待彼此,優雅地為別人讓道,面帶微笑,心中懷著一種聯結感,一種和諧的、共融的感受。」
「這就是古典音樂的效力,這也是我們的希望。」畢格說。◇
------------------
📰支持大紀元,購買日報:
https://www.epochtimeshk.org/stores
📊InfoG:
https://bit.ly/EpochTimesHK_InfoG
✒️名家專欄:
https://bit.ly/EpochTimesHK_Colu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