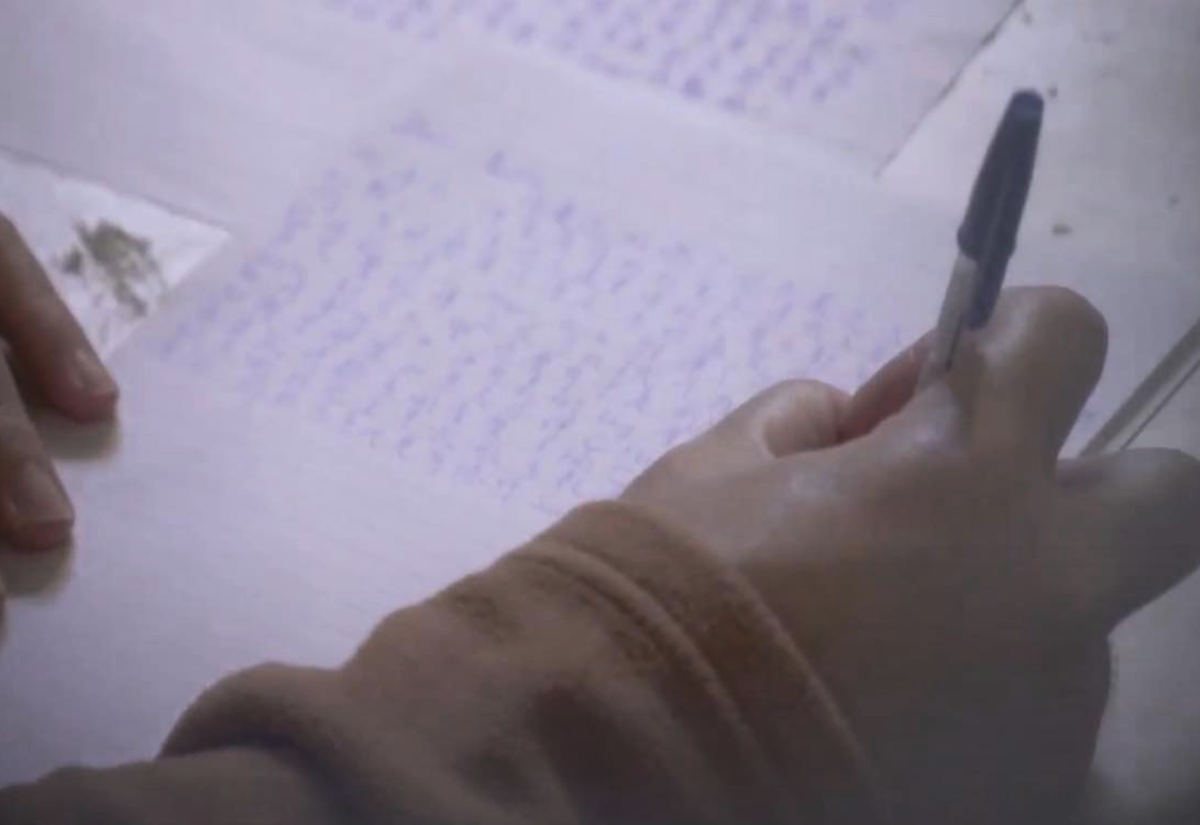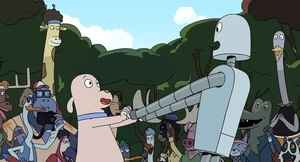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在電台節目說,曾接觸多名因反修例示威而被捕的青年,他們均感後悔,更引述一名在囚青年的話:「佢(母親)花大半日嚟探我,而且次次都好堅持嚟,想到呢度我心裏面好難受,𠵱家我先發現呢個世界,邊個係真正對我不離不棄嘅人,就只有我阿媽,而唔係啲咩手足。」
正如2019年林鄭月娥也聲稱跟「前線手足」對話,我自然不懷疑蕭處長與在囚青年有接觸。我看不透的是,處長引述該名青年的話,到底想向公眾發放甚麼訊息呢?想暗示「手足」無情無義,把在囚者拋諸腦後?
早前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振振有詞,指監獄內外有人互相勾結,意圖利用朱古力、髮夾等收買人心,從而建立勢力,從而「危害國家安全」。蕭澤頤應該很清楚,如有「手足」對在囚青年不離不棄,就等於犯了官方定性的「在獄中建立勢力」、「煽惑抗爭」等「罪行」,保安局和懲教署會容許嗎?
牆外有熱心市民寫信「鼓勵」在囚者,就罵人要「建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到沒有信寄去了,就暗諷被「手足」離棄。我不禁想起某些古惑仔的行徑:你路過時望他一眼,他就指著你大罵:「睥咩呀睥,未死過呀?」你不望他,他又指著你怒吼:「做乜唔望我,想死呀?」
人在監獄內,即使是通信這樣平常的事,也不再那麼理所當然。很多話都不能講,因為會被審查;有些信就算寄出,也不知甚麼時候才到達對方手裏。曾看過一本英文書,講述二戰期間戰俘被關押在香港和日本的日子,書名叫《長夜到白日之旅》(Long Night’s Journey into Day),作者為Charles G. Roland,有一章講寄信,我特別難忘。
當時香港淪陷,日軍關押一批英國、加拿大戰犯,他們最盼望的,就是跟家人儘早通信聯繫。但寄信卻有重重關卡,極不容易。由於每封信都要通過日本人審查,而營內翻譯人員又寥寥無幾,導致審查程序曠日費時,寄出遙遙無期。戰俘們有時經過日本人的辦公室,總看到牆角堆滿一袋袋從獄中寄出的信,月復月都是同一個袋,同一堆信。
為了節省翻譯員做審查的功夫,日本人於是預印了一疊卡片,上面寫著「I am well...working hard...in hospital」,囚犯不能自己寫字,只可刪除某些單詞寄出。有些囚徒為了讓家人安心,即使在醫院病得很重,也會刻意選取「I am well」此項。
除了寄信,比較令我意外的,是日本人還容許戰俘透過無線電廣播跟家人聯繫。1942年6月,10名關押在北角的加拿大戰俘,先乘巴士到碼頭,轉渡輪往九龍,然後搭巴士到達日本總部。日本人安排他們對著麥克風講幾句話,這些話錄音後就廣播開去,透過美、加的業餘無線電操作員,迂迴曲折地傳送到囚犯的家鄉。為了傳這個簡單的短訊,他們竟花了5小時來回,還錯過晚飯,折騰半日,其間只喝到日本人給他們的兩杯淡而無味的綠茶。@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 http://www.patreon.com/sefirot
( 本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
------------------
【噤聲時代,更需要真相】
一起守住心中最後的光:https://bit.ly/3t45Qni
✅立即支持訂閱:
https://hk.epochtimes.com/subscribe
✅直接贊助大紀元:
https://www.epochtimeshk.org/sponsors
✅成為我們的Patron:
https://www.patreon.com/epochtimeshk
------------------
📰支持大紀元,購買日報:
https://www.epochtimeshk.org/stores
📊InfoG:
https://bit.ly/EpochTimesHK_InfoG
✒️名家專欄:
https://bit.ly/EpochTimesHK_Colu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