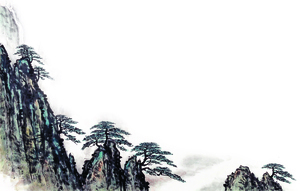昭雪從小嬌生慣養,父母慈祥,還從未得過如此當眾喝斥,登時含淚,退到母親懷中。
昭鶴亭轉笑,對高義薄道:「小女無知,是弟調教無方。不知令公子若何,在哪裏高就?」
高義薄忽然面現慍色,道:「那不肖子,當真氣煞我也!賢弟不是外人,我說與你聽也罷。去年正月,犬子打算上京赴考,我便予他盤纏、小廝,一同路。」
昭鶴亭道:「胸有大志,不減其父當年。但是為何既入京城,不來找賢弟呢?」
高義薄擺擺手,道:「哪知這混帳小子,一路上吃吃喝喝喝,到處遊山玩水,待到得京城,盤纏所剩無幾。當了棉衣,進了賭坊,輸得一文不剩。怕小廝回鄉說與我聽,竟把小廝賣了,可憐那小童從小便跟著我,現竟不知流落何方。後來整日在街上遊蕩,與乞丐無異。更沒臉來拜見叔父,唉,這個混帳!」
小梅在一旁聽得偷笑,昭雪也用帕子掩住了口。
昭鶴亭捋著鬍子,緩道:「這個孩子還是有些骨氣的。」
高義薄道:「本來家醜不外揚,但見侄女兒如此端莊賢淑,我那不肖子,只恐配不上。」
小梅悄悄說與童子:「那簡直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昭鶴亭一忖,道:「既然是指腹為婚,便是一諾千金,不可更改。想我那侄兒,本性不壞,稍加指點,日後必成大器。」
此言一出,滿堂無聲。小梅氣得直瞪眼,昭雪眉心似重鎖,昭夫人緊緊攥著女兒的手。
高義薄忽然起身,拱手道:「天色已晚,我還有公務在身,先行告辭。」
昭鶴亭道:「既是公務,不便強留,閒時得空,再為兄長接風洗塵。」
高義薄道:「賢弟既然如此盛情,愚兄過幾日再來叨擾,賢弟這幾日都在家中嗎?」
昭鶴亭道:「在,都在,兄長可隨時賞光,弟也期與兄長一同把酒敘談。」
說罷,直送到大門外,見他人上轎離去,方才回到內堂。誰知剛 一進內堂,昭夫人便哭哭啼啼撲將上來:「老爺,你可不是貪圖富貴的人啊!不能將昭雪嫁給那個浪蕩子啊!」
昭鶴亭道:「夫人!君子一諾千金,豈有反悔的!她便是你女兒,也是我女兒。你放心,我聽聞那高公子本性不壞,只是少了良教,日後加以教導,定能成才的。」
昭夫人點了點頭,含淚道:「她是你女兒,你便親自說與她聽去吧。」
「也好,昭雪人呢?」昭鶴亭道。「小姐回房了。」童子道。
昭鶴亭向後堂走去,在女兒閨房外緩聲道:「昭雪,為父當眾斥責你,是為父的不是,爹爹給你賠罪了。」
房門一動,昭雪走了出來,款款一拜:「爹爹,您這是做甚麼。女兒承受不起。」
「你隨我來。」昭鶴亭道。父女二人來到了雅室,童子奉茶退下。
昭鶴亭道:「可知為父為何斥責與你?」昭雪搖了搖頭,忽的想起了甚麼,道:「是我說了那曲子的名字?爹爹,你是怕那人知道,所以......」「不錯。」昭鶴亭點了點頭。
「女兒不明白,爹爹您不是常誇讚那曲子音韻諧和、淨人雜念、好似天音麼?又為何如此怕人知曉?」
昭父道:「雪兒,你聽我細說給你聽。」
詳言一炷香時間,昭雪點了點頭,道:「原來這是禁曲。可是爹爹您常常彈起,也並未見異樣啊?反倒更精神了呢!古人云,樂者,藥也。想來是正始之音,才能有此奇效。」
昭父道:「所以,該便是樁天大的奇冤。兩年已過,我至今參詳不透,如何就成了邪音。君子在世,當頂天立地,真假不辨,良言不吐,為虎作倀,與禽獸何異?」昭父言之動容,嘆道:「我已年過半百,人生足矣,只一留戀,便是你這孩子。高家與我們世代交好,公子雖不才,但到底是官宦人家,未嘗不是一個庇所。萬一哪天,我......」
昭雪秀眉緊蹙,道:「爹爹,休要再言。只恨吾是女兒身,不能頂門立戶。但請爹爹放心,爹娘養育女兒多年,雪兒終生不嫁,也要服侍二老天年。」
昭父一甩手道:「丫頭糊塗啊!」說罷,各自沉吟,半晌不語。昭父走到木琴旁坐下,嘆道:
「為父將這首曲子教你吧,也好傳於後世。但是,你須答應我,不能彈奏給旁人聽,免招殺身之禍。」
昭雪似懂非懂,點了點頭。
昭雪天資不淺,是夜便習了半首,留下半首,次日再習。◇(待續)
------------------
📰支持大紀元,購買日報:
https://www.epochtimeshk.org/stores
📊InfoG:
https://bit.ly/EpochTimesHK_InfoG
✒️名家專欄:
https://bit.ly/EpochTimesHK_Colu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