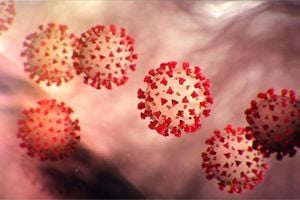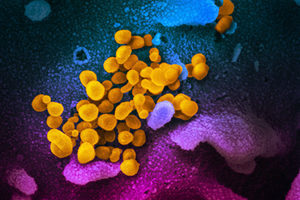隨著中共肺炎(俗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加劇,醫學界對病毒的來源也越發關注。多份近期發表的專家報告分析病毒的結構和特性,並有質疑其可能是實驗室人工合成。白宮已要求美國科學家研究該病毒的來源。
本期《熱點互動》節目專訪歐洲病毒學專家董宇紅,分析解讀專家近期發現及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特點;並呼籲中共透明公開資訊,讓全球專家參與抗疫。
董宇紅 :北京醫科大學醫學學士;北京大學傳染病學博士;曾是北京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醫生。有17年抗病毒臨床和研究經驗。曾在諾華研發部門(Novartis)任職;現任瑞士生物技術公司SunRegen Healthcare AG首席科學官。
【專訪】歐洲病毒學專家:中共病毒有很強人工干預痕跡,似在實驗室產生;病毒有很強傳播力和毒性;中共必須透明,讓全球專家參與抗疫
主持人:觀眾朋友好,歡迎收看這一期【熱點互動】周末特輯。隨著武漢中共肺炎疫情的加劇,醫學界對於病毒的來源也越發關注。近期有多份醫學報告發表,都在研究這個病毒的結構和特性,並且質疑病毒似乎有人工干預的痕跡。美國白宮也要求美國科學家研究這個病毒的起源。歐洲病毒學專家董宇紅博士近日在《大紀元》上發表文章,探討這方面的問題。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董宇紅博士,來跟我們分享她的研究和發現。
董宇紅博士是北京醫科大學的醫學學士、北京大學傳染病學博士,曾經在北京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工作,有17年的抗病毒研究和臨床經驗。她曾經在世界三大藥企之一的諾華製藥研發部門工作。現在董宇紅博士任職於瑞士一家生物技術公司的首席科學官。今天,董宇紅博士,我們很高興能夠通過skype和您連線,感謝您參加我們的節目,您好。
董宇紅:主持人您好,觀眾朋友好。
主持人:好,謝謝您的參與。我們就直接來談一談這個大家都在關注的問題。董宇紅博士我知道您最近在《大紀元》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那這篇文章就是您分析了近期一些醫學報告裏面的發現和研究;然後您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說這種「新型冠狀病毒」(中共病毒)具有前所未有的病毒學特徵,表明這種病毒的自然發生機率是非常罕見的。換句話說,我的理解是人工干預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我想先請您談談,您怎麼會想要寫這樣一篇文章?然後您是如何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的呢?(註:董宇紅博士文章中譯版:https://www.epochtimes.com/b5/20/2/3/n11842176.htm)
董宇紅:我本人就是搞傳染病出身的,然後自己的80多歲的高齡父母,還有很多的親人、兄弟姊妹都在黃岡和武漢,也就是最早一批封城的城市。今年大年三十(01/24)給父母拜年的那一天,父親就說封了城了。以前過年是開門大吉,今年是關門大吉。然後武漢和黃岡封城之後,所有的親戚朋友的群都非常的緊張,聊天的這個群。原來過年一般都是最熱鬧的時候,大家互相串門子,走親戚啊,互相說一些祝福的話。
今年非常的相反,所有的親戚朋友都在家裏,氣氛搞得很緊張。然後我才意識到出了事,就趕快看新聞。其實2003年的非典(SARS)的時候我就在北京,那時候我還生病,住在北京市中心的一個大醫院大概一兩個月。那時候的氣氛也有點緊張,但是其實根本沒有辦法和現在的武漢肺炎(中共肺炎)相比。人們戴著口罩,基本的出行和交通稍微有一點戒嚴,但是沒有「封城」一說。這個武漢的肺炎被哈佛大學的流行病學家埃里克.費格丁博士(Dr. Eric Feigl-Ding),被稱為是「熱核武級的瘟疫」,它的R0(基本傳染數)指數是非常的高,估計感染人數至少在六位數左右。
解讀多份醫學報告 中共病毒具有前所未有特徵 4關鍵點被替換
《刺針》(The Lancet)雜誌的最近的一篇醫學,對41例臨床病例的醫學觀察報道,1/3的人是需要ICU(加護病房)重症處理的;一半的人以上出現呼吸困難,還有15%的這麼高的一個死亡率。那憑著醫生的職業敏感,我馬上就感覺到這個疫情非同尋常,可以說是來勢洶洶。
那出於對父母、親人還有朋友,以及全國人民的擔心,我非常自然地就問自己,那這個病毒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為甚麼它這麼毒?那作為一個科學研究出身的人,我自然地就是先去查文獻。看看科學家們都做了哪些研究。
比方說臨床的研究,還有分子生物學的基因的研究,這就是科學研究的自然的思路。那我當時找的文章大部份都是來自國際頂級醫學和生物學期刊發表的文章,比方說《刺針》(The Lancet)雜誌、《科學》(Science)雜誌、《自然》(Nature)雜誌等等。
而且基本上都是中國的醫生和科學家的一線的資料、第一手的資料。而這些中國的科學家來自中國的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預防所、國家生物安全重點實驗室的專家等等,另外還有武漢的金銀潭醫院的一線醫生等等。那這些數據是非常可信的。
因為這些病毒的序列上傳到了一個國際基因的數據庫,所以國外學者也非常關注,他們也拿這些序列進行電腦的模擬研究,也發表了他們的研究數據。那做這個研究我的宗只旨是保持一個客觀和公正性,我不受任何其它的非正規渠道消息的影響,只採用正規渠道發表的論文。那基因檢測的技術現在非常成熟,而且是一個「硬數據」,查到的這個序列是甚麼樣的,它就是甚麼樣的,這個真實性、可靠性都非常的高。
本著這個實事求是的態度,我大概讀了十幾篇文獻,最後選出比較有代表性的,然後把我所看到的這些文章報道出來的一些現象,總結歸納了一下。我本人拿出來跟大家共享的目的:是為了促進科學的探討,促進學術的交流。
主持人:是,請講您的發現。
董宇紅:比方說,每當科學家發現一種新病毒的時候,他自然地就會把這個病毒拿去分析它的基因序列,這是要做的第一件事情。通俗地講,就是追本溯源;看看這個新病毒和已知的病毒之間的序列的差異性有多大?根據它這個序列的相似性來歸結歸到目前已知的病毒的「門、綱、目、科、屬、種」(生物分類法),那這個是一個非常基本的思路。
我看到的這些論文大部份都指出來:這個武漢的新冠狀病毒(中共病毒)雖然現在分類到了「冠狀病毒」(Coronavirus)這個家族,但是它像是一個「非常新」的成員。即使以最親近的,所謂的有兩顆來自蝙蝠的冠狀病毒,很靠近,是最靠近的,也就是說這個家族中的最近的親戚,比較接近。但是它全基因組序列的相似度仍然不高。
這個就讓人們,這是讓我警覺得第一個訊號,讓我覺得這個基因,因為基因決定了蛋白質,蛋白質決定了功能。所以基因既然相似度不高,那它可能很多其它方面就要進一步去探尋,所以這是我發現的第一個疑點所在。
第二個,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病毒是一個寄生物,它自己是不能單獨存活的,它必須要在宿主細胞裏面才能夠生存。那它怎麼進入到宿主的細胞裏呢?這就需要有一個受體,和這個病毒表面的蛋白相結合。那病毒表面有一個蛋白,這就像鑰匙一樣,那細胞表面也有一個蛋白,這就像一個受體,所以就像一個鎖。鑰匙開鎖這個原理,就跟這個病毒的表面蛋白跟那個細胞表面的受體結合的原理很相似。病毒跟它受體結合之後,那個受體細胞就發生一種內吞噬的作用 (phagocytosis),把病毒以及整個病毒顆粒都包進去,叫內吞作用(endocytosis)。這樣這個病毒就成功地打入到了宿主的機體的細胞裏面去,從而在它(宿主)裏面利用這個宿主的細胞的這種結構和蛋白質,這些酶、這些系統進行它(病毒)自己的生命周期和復始。這就是說病毒是一種非常狡猾的微生物。正因為它(病毒)的這種攻入細胞內複製的能力,才使得現在抗病毒的藥物的這個治療非常難,開發很難。
那這個冠狀病毒它共同的一個特點,就是它們表面都有一個關鍵的蛋白叫S蛋白,也就是叫所謂的棘突蛋白(Spike Protein);這個棘突蛋白是公認的冠狀病毒侵入人體細胞的一個表面的蛋白質,那這個蛋白質在感染宿主的這個親和力,還有它的發揮毒力方面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我們就來關注一下這個重要的S蛋白。
這個蛋白質,我看到的這些論文中,都提到了一個共同的研究現象,這個S蛋白的基因片段,和其它這個病毒非S蛋白區域的其它的基因片段非常不同,序列非常不同。假設這個病毒的其它的蛋白和其它的同類的冠狀病毒,假設是80%-90%的相似性,這個S蛋白和其它的基因的冠狀病毒的S蛋白的相似性只有70%,差異非常的明顯。
而且最關鍵的在哪裏呢?就是這個S蛋白的序列中間有一個讓人非常困惑,找不到任何來源的一個中間序列;許多學者都分析分解報道這個序列,大概有幾千個bp(base pair),就是鹼基對,這個序列在所有病毒的數據庫裏都找不到。所以這個也是讓人感到非常奇特和驚訝的一個地方。
第三個,這個酵體蛋白S蛋白的基因不同,它的蛋白質結構方面也有一些不同,其中有兩篇論文發現S蛋白的,我們知道蛋白質是個三維結構,有些基因表達序列是在裏面的這個意義性就不是很大;有一些序列就是在蛋白質的表面,起到跟其它的受體結合的一些關鍵的位點。
這個S蛋白有兩篇論文都提到了,在它的表面有關鍵的四個胺基酸被替換了。而且替換之後,居然它不改變S蛋白和它受體之間的親和力。其中一篇論文來自於中國科學院巴斯德研究所的專家崔傑,還有一篇來自於印度的印度理工學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普拉丹(Pradhan)教授,印度的團隊報的是跟HIV結合的一個受體,中國的專家報的是跟ACE2,就是人的血管緊張(收縮)素轉化酶2(ACE2)轉回系統一個受體的結合力。
我們就說這個基因的突變,尤其是病毒這種基因的突變有兩種:一種是自然突變,這種突變一般都是隨機的,沒有任何的功能性或者目的性,它是叫漂變(genetic drift),大部份叫漂變,或者叫自然的病毒之間重組。我們看到這種精確的定點突變,能夠保證它的受體蛋白的功能,但是它又保證它突變的準確性,這一點讓人就很驚訝。
這個病毒為甚麼能夠精準去突變?而且能夠保持它的功能不變?這個在自然界中出現的概率,不能說沒有,但是作為搞病毒的專業的生物學家來講,觀察到這種現象的概率非常的小,非常的小。所以幾乎是有兩篇文章,幾乎都是拒絕了這個病毒是來源於自然重組的,這麼一個假設。
中共病毒pShuttle插入痕跡明顯 留下「不可抹滅人工參與痕跡」
主持人:好。因為您講到這裏,我想起在您發表這篇文章之後,您跟另外一個美國科學家James Lyons-Weiler也有了一個通話,那位科學家是從不同的角度去研究這個病毒,但是得出了類似的結論。能不能請您跟我們談一下,那位美國科學家的結論和他的依據是甚麼?
董宇紅:這位美國的科學家是長期從事生物基因組分析的一個專家,而且他研究過伊波拉(Ebola)病毒的爆發。他從疫情發生以來就高度地關注這個新冠病毒(中共病毒),自己通過國際共享的病毒序列庫,做了很多獨立的病毒序列的研究,其實在我寫那篇文章之前,他已經在他的網誌裏面發表了好幾篇,關於他獨立的一個發現。
我也是很巧,就在把自己的文章總結出來的第二天,也讀到了他網誌的文章,然後馬上就聯絡了這位專家,並且跟他連線溝通,對話大概兩個鐘頭。首先第一點,他也是從基因的序列的分析入手,發現棘突蛋白(Spike Protein)跟這個病毒(中共病毒)的其它基因所編碼的蛋白質非常不一樣。
他的原話是這麼說的:為甚麼在這個病毒(中共病毒)的基因裏頭,這麼多基因裏頭只有編碼這一個蛋白質的基因會有如此大的序列的差異?這個沒有道理。除非是來自於其它的地方,因為棘突蛋白(Spike Protein)和其它基因組的蛋白差異確實使棘突蛋白(Spike Protein)十分的與眾不同。
他是搞進化生物學的專家,所以看到了這個不同,覺得非常的詫異。他認為的一個最有利的證據,是來自於中國科學家發表的第一篇關於這個病毒基因序列的報道,這個文章是說,原來假設是這個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的基因,是跟已知的一個序列相匹配的。它原來是來自於蛇,做了這樣一個假設,但是後來這個假設被推翻了。就是因為這個中國科學家也是發現了S蛋白裏頭有一個沒有任何匹配的一個基因序列,所以就人為地去假設,可能是跟蛇的一個甚麼冠狀病毒的一個序列,可能有相關性。但是後來這個假設在James博士看來,顯然已經被推翻了,是不成立的。
James博士就繼續根據他的分子生物學的基因分析方法,去找了一些非病毒來源的序列,把很神秘的這一段序列拿去跟其它非病毒來源的序列做比對。他發現有一種用來做重組SARS,棘突蛋白(spike protein)的研究的載體,叫pShuttle-SN載體的序列非常的接近。甚麼叫pShuttle呢?Shuttle咱們都知道Shuttle bus(接駁車);Shuttle顧名思義就是運輸工具的意思,就是在基因工程技術裏面,它就是把一個物種運到另一個物種的意思,它就像一種基因的運輸工具。發明pShuttle-SN的實驗室,就是來自於中國的一個做SARS基因疫苗蛋白的一個實驗室。
所以James博士最後他的結論就是:他並不認為這個一定就是有意製造的一個生物武器,或者甚麼的,他不認為可能是這樣。但是他的的確確認為,在我們實驗室中,有可能是因為基因重組,可能會產生一些非常危險的病毒,這些病毒就是因為我們把一個病毒的某些序列放到另一個病毒的某些序列上,最後人為地產生出一種人工的重組病毒。人工的重組病毒,可能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個毒性。
主持人:因為我看到有人對這篇文章評論,就是pShuttle插入的痕跡很明顯,就像留下了一個指紋一樣。是這樣嗎?
董宇紅:對的,這個pShuttle在病毒大類裏頭,在生物裏頭是沒有的,這個序列一般是用來做基因重組技術的指令,載體的時候才會用到的。這個就像人的指紋,每個人的指紋都不一樣,每一種生物它的基因的某些序列,有些很特別的,特徵性的序列也不一樣,所以相當於留下了一個「不可抹滅的人工參與的痕跡」。
主持人:所以James博士的結論是甚麼?
董宇紅:James博士結論是:這個新冠病毒(中共病毒)有90%~95%的可能性,是由一個「實驗室的事件」所引起的。所謂的「實驗室事件」就是指人工改造病毒的實驗室,就是lab event,而不是一個來自於天然的。
白宮要求科學家研究新冠病毒起源 美國應起主導作用
主持人:我覺得您剛才講的都是非常重要,雖然說有很多科學的術語我們觀眾不一定能聽明白,但是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我想請您談一下,現在白宮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OSTP)主任在致美國國家科學,工程和醫學研究院的一封信中,要求科學專家「迅速」研究病毒的起源。而且在這封信中提到了一些最近的研究報告,顯示出一些很有爭議性的東西。您覺得白宮這樣的表態,您怎麼解讀呢?
董宇紅:我毫不意外,而且甚至可以說是一直在期待。因為中國這個疫情是相當嚴重的,可以說是一場災難,突如其來的災難。到現在很多的關於病毒本身的生物學特性,包括它(中共病毒)是如何傳播的?它的基因片段、它的功能蛋白、它的毒性指數,還有動物學實驗和臨床上的研究都不清楚,數據都不清楚,讓人毫無準備。
所以每天看到這麼多的人去世,是非常痛心的。那麼這麼重大的一個全球公共衛生事件,不僅是中國,對全球都有可能造成威脅。美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有著全世界一流的搞病毒方面的研究,流行病學方面的防控的科學家,它(美國)應該從政府層面正式的關注這件事。這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而且它(美國)應該有責任去盡一切努力,幫助中國和世界解決這個問題,平穩地渡過這場災難。
不僅僅希望美國,其他的科學家、有能力的、其它的國家,我都希望它們也能夠關注這件事情,甚至也能夠派出它們的醫生、科學家的專業團隊,甚至能夠到中國的疫區,來幫助中國的一線醫生,包括幫助中國的科學家們來抗擊這場疫情。所謂「唇亡齒寒」,中國的危難不僅僅是中國一個國家的事情,中國的災難就是全世界人們的災難,中國的問題也將會是全世界人們的問題。
病毒如是人工合成遭洩露 相關者一定要被追責 科技發展應以道德為準繩
主持人:所以我們來做一個假設,雖然說聽起來難以置信;但是從科學方面您剛才談到了,真的有科學家認為這很可能是一個人工干預的結果,甚至實驗室的疏失造成這樣一個結果。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這麼大的事件,誰該負責?人們應該怎麼應對?
董宇紅:這個話題很沉重。我們知道現在生物學技術已經發展到了基因工程和基因改造的技術環節來了;其實過去的幾十年來科學家已經能夠用各種各樣的基因重組技術來改造病毒、重組病毒,利用這種技術來造新的病毒、新的疫苗或者是研究病毒的某些生物學特性,甚至是基因治療法來把某些有益的蛋白導入到人體,來做一些基因療法等等。這些似乎都是對人類有益的事情,而且確實是科學界現在最熱門的一個話題。
但是「辨證」地來講,其實任何事情都是一把雙刃劍。比方說我就看到有一些論文,它就用一個基因工程技術製造出一個「嵌合病毒」(Chimera virus),它把來源於一種野生的病毒的一種很毒性的一個蛋白,嵌合到另外一種已知病毒中去,然後研究移過去的基因編製的蛋白,在新的病毒裏面的毒性。這些技術其實都不是為了研究,說白了都是為了做分子生物學的研究。但是這種新造出來的這些病毒,它有可能毒力更強,而且會造成一些對人類潛在的更大的威脅。
比方說美國的一個分子生物學家和生物防疫專家Richard Ebright在2015年發表在《自然》期刊上,對於用到這種病毒重組技術造成新病毒的文章就提出了質疑。他認為這項工作唯一的影響,就是在實驗室中製造一種新的非自然的風險。這就關係到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的肺炎,剛才提到的James博士他有一個假說,他就認為:有可能是跟SARS的疫苗的研究有關係,跟它(中共病毒)關聯起來。
因為SARS疫苗也是用基因重組技術做出來的,我們先不去追究這個病毒到底是為了甚麼目的,是出於科學的動機也好,或者任何動機也好,怎麼造出來的也好;我們就感覺到「這個實驗室」既然造出來,它就要負責任,就要確保有毒性的病毒不能夠隨意地洩漏。如果一旦「洩漏」,對公眾造成的影響將會是非常大的,甚至是災難性的。
我認為科學的發展固然非常重要,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科技的良性的發展也要建立在一個對人類有益的,甚至維繫人類的基本道德的這麼一個層面上。否則的話,如果只是一昧地發展科技,而忽視人類的基本道德建設的話,那看似繁榮的科技發展卻會隱藏巨大的危機。甚至人類會因為自己的科技過度發展而吞食苦果。
此次疫情中頻頻出現有人倒地是怎麼回事?
主持人:是,這確實是一個相當大的話題,我覺得值得人們思考。我想接著問您一些比較具體的問題,比如說這一次的疫情中,我們看到一個很不一樣的現象,就是在各個地方都會看到有人突然倒地;我們看到街上頻頻發生,網上流傳的影片也滿多。這讓人覺得非常驚駭,這是怎麼回事?就是這些突然倒地,背後有可能是甚麼原因造成的?這些突然倒地的人是昏迷了,還是死亡了呢?
董宇紅:我也是看到了這些影片,非常多,大概至少有十幾個吧,這個現象讓我感到非常的怵目驚心,從醫在醫院工作大概6年,非典(SARS)期間也見識了當時的疫情,在我的從醫生涯中從來沒有看到這種現象。從這些錄像上來看,這些人都是手裏提著購物袋或者拿著行李箱,或者甚至就在公共場所,做他的工作,突然一下子⋯⋯,錄像裏表明他就倒下去了。甚至倒在地上一動不動,也沒有發生甚麼⋯⋯。
主持人:也沒有掙扎。
董宇紅:對,也沒有掙扎,不像是疼痛或者一種痙攣,或者是肌肉的抽搐甚麼的,局部的肌肉的痙攣造成的一種行動的障礙。而更像是一種心臟或者是肺臟功能直接的衰竭,所謂的「心肺功能衰竭」。因為人死之前是兩個臟器衰竭了,一個就是心臟,一個就是肺臟。心臟不能工作了,沒有辦法把血液輸送到全身;那肺呢,不能進氣、不能出氣,沒有辦法把氧氣輸送到全身。這兩個臟器如果是同時衰竭,這個人就可以定為死亡了,就是死亡。我不能下定論,現在數據太少,其實需要屍檢報告。
第一,我們需要這些猝死這些案例,最好當局就是中國的衛生當局提供一個完整的系統的,最少要做幾十例屍檢的報告,得出一個到底他們是哪些臟器的原因,這個是要做屍檢、要查明的。第二,從簡單的急診醫生急救醫學的常識,分析出心肺功能的衰竭,另外從《刺針》(The Lancet)雜誌的這個臨床研究的觀察來看。
這個病毒(中共病毒)有一半以上感染這個病毒的病人,都有呼吸困難,有12%出現急性心臟的損傷,那病人有60%幾,出現急性淋巴細胞的減少。那多半是由於這個細胞因子,還有很多的細胞因子釋放到血液中。這個細胞因子,說白了就像砲彈一樣,它可以攻擊全身各個臟器的細胞,導致全身多臟器功能的衰竭。所以這個病情這麼重,看起來是跟這個臨床觀察的研究,看起來還是比較有關聯的,比較接近的。但是總而言之,太怵目驚心,太痛心,也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猝死現象。所以只能說是我個人一些的粗淺的認識,希望科學研究的正式報告出來,才能夠得出進一步的判斷吧!
不斷發現有關病毒的新現象 這是個甚麼樣的病毒?
主持人:好的,說到這我也想請您談一下,這個病毒(中共病毒)本身,因為我們最近有看到有關這個病毒的一些新的發現不斷的出現,甚至可以說是不斷的變異。比如有報道說:不戴口罩幾十秒就能傳染;還有甚麼無症狀傳播、母嬰傳染、包括現在中共官方承認它可以通過過氣溶膠(aerosol)傳染⋯⋯這個病毒(中共病毒)到底是甚麼樣的病毒,從您病毒學專家的角度來看?
董宇紅:一個病毒對人體的危害性主要有二方面的指標來衡量。一個就是「傳播性」或者叫「傳染力」,也就是在人群中擴散的能力,感染人的速度和能力。第二個就是它的「毒性」。那您剛才提到的這個問題呢,就是這個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的傳播性。
那我們從已知的來自中共政府官方的這個聲明,它們已經正式承認,這個病毒有二個傳播的途徑。第一,就是跟SARS很相似的飛沫傳播。所謂的「飛沫傳播」就是指病人感染這個病毒的病人,他呼吸道口腔或鼻腔出來的飛沫。這個小的飛沫它飄浮在空氣中,那一般來說就是離這個病人比較近的人會比較容易傳染上。
另外一種就是「接觸」,就是直接跟手。因為這個飛沫既然能傳播到外面,那這個病人本身的身體各個部位可能也沾上了這個病毒的飛沫。那別人跟他(患者)去握手可能也會通過這種直接的接觸,把這個病毒帶到他(接觸者)的身上。所以這是跟SARS當時也是主要靠這個方式傳播,這是跟距離有關聯的。這叫「近距離接觸範圍」。一般是5米到10米左右的這個範圍的飛沫傳播。
那這個新冠病毒(中共病毒)它可怕在哪裏呢?它還有一種傳播方式,叫作「無接觸的傳播」,這是中共政府官方的陳述。「無接觸的傳播」是甚麼呢?它在飛沫裏面會形成一種氣溶膠(aerosol),就混合在空氣中懸浮在空氣中,成為很小的這種氣溶膠(aerosol)的顆粒,隨著空氣的流動或者是風飄向更遠的地方。那這種氣溶膠的傳播,它就跟距離近距離接觸沒有關聯了,那它就可以播散到很遠。
這個換句話就是說,它(中共病毒)可以「遠距離傳播」。這個我們聯想到現在疫情擴散的速度,還有這個公眾的恐慌。其實這個氣溶膠(aerosol)的傳播是可以解釋它(中共病毒)的傳播能力的。
主持人:您說的遠距離傳播大概會有多遠,有一個估計值嗎?
董宇紅:目前在我接觸過的傳染性病毒的病例中,我好像還沒有見過這種遠距離氣溶膠(aerosol)傳播的案例。所以現在不好講,但是它肯定是比近距離的個位數的米要大得多。所以當時武漢為甚麼封城?為甚麼不說我們就先戒嚴一下,把一些關鍵的地方如醫院把它給封鎖起來就行了?而是一下子就「封城」了?我們就可以想像到可能政府已經看到了這個病毒傳播力太廣、太有力了,或者說太強悍了。所以就是說這個距離會很遠,那幾十米幾百米甚至更遠都有可能,所以這個就是很難去控制的。
那這個病毒(中共病毒)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人傳人非常強,另外它在潛伏期就可以傳播。因為我們搞傳染病的一般都知道,一般病毒性的傳染病它是要在發病期,有症狀的時候它才有傳染性。因為在發病期的時候病毒在體內的毒性含量相對的數量是最多的,那在這個時候它才可以傳播。
可是這個新冠病毒(中共病毒)它在潛伏期就可以傳播。那換句話說,很多人出現在公眾場合的時候,你就不知道他到底帶沒帶這個病毒。這就給疾病的篩查、防控帶來非常大的難度。你就沒有辦法去監控這個病毒,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你總不能說把每個人都拿來查一遍,那會增加相當大的衛生部門的壓力。所以這是它(中共病毒)的傳播力。
第二個,根據它這麼嚴重的臨床表現。這個病毒顯示了相當大的毒力,甚麼意思呢?就是臨床的「危重病例比例高」,病死率高。我記得SARS當時的病死率大概是9.3%,然後根據最近《刺針》(The Lancet)雜誌的這個41例的病史例報道,病死率是15%;而且重症、無症狀的患者突然死亡。這些都是這個病毒對人的危害和毒性比較大的這幾個地方。
另外還有相當大的一部份患者,他的血液淋巴細胞的下降,有63%的患者,那這些都是臨床上表現不一樣的地方。那既然它(中共病毒)毒性大,毒性是來自於病毒的蛋白質的功能和特性。這就是為甚麼我又提到了,研究這個病毒基因的重要性。因為S蛋白它是決定這個病毒的傳播力,就是這個S蛋白使得這個病毒能夠綁定到人體的細胞中去,那決定了它的傳播力,也決定了這個病毒的毒性。所以一定要大力地開展這方面的去研究,到底是哪些蛋白質導致它的毒性?跟哪些受體?哪些細胞去結合?導致它這麼大的傳染性和毒性。這是一定要搞清楚的。
中國及世界正遭遇危機 中共一定要透明 讓全球專家參與抗疫
主持人:我想問您最後一個問題,作為一位醫生和科學家,您怎麼看中共政府近來對這個疫情的處理和應對。另外總的來說,您怎麼看這次疫情?
董宇紅:我們實事求是地承認吧。中國其實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一個危機和災難。中國(共)政府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公開數據,把它知道的這些病例、這些研究給它公開,向國際社會公開。只有這樣國際社會上的科學家、醫生,還有各國的資源才能幫得上忙。
這個全新的病毒對人類造成了這麼大的威脅,而且現在對這個病毒本身的基本的生物學的特性都沒有認識清楚。我們中國有句話:「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我們現在對這個敵人,這個新冠病毒(中共病毒)連它本身到底是個甚麼樣的病毒學的特性?它的毒性特徵、它的來源,包括它最初的來源、它的傳播力、傳染性、對人的各種器官組織的危害,這些都不清楚。
那我們就無從下手,在防治上,只能根據傳染病防制的基本原則。隔離保護,保護易感者,隔離,然後切斷傳播途徑。但是對這個病毒本身來講,那我們毫不清楚這些情況。所以希望這些數據能夠儘可能地去公開。
並且要接納國際社會的援助、人道主義的援助。尤其是現在這個病例,我前二天看到的這個病例,還處在一個(上升階段)。衡量一個傳染病是否平穩,要看它的每日新發病例是否還在增長。那現在是每日的新發病例還在以千位數的數字在增長,那現在這個病情還在上升中。
那這個感染的病例到底有多少?有多少是帶毒者?有多少是輕症感染者?有多少是中等程度?有多少是重症?⋯⋯這些情況都不清楚。還有救治情況,他們是怎麼處理的?死亡原因?⋯⋯等等等等。
所以這是一個艱巨的一個抗災工程,一個艱巨的需要全世界的科學家和全世界的醫生和政府相關人員來共同解決的一個課題。不是中國,我呼籲世界上有能力的科學家,儘可能地在做科研的同時。我也呼籲中國(共)政府能夠把疾病防控真實的資料和數據,公開發表到全世界的數據庫去。實事求是地接納國際社會的援助和幫助。
主持人:好的。
董宇紅:另外呢,這是人命關天的事,而且事關重大。作為一個醫生來講,醫生的責任就是救死扶傷,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值得珍視的,都是非常寶貴的。那中國發生的這場災難可以說是一個重大的人道主義災難。這對每一個人都是一場檢驗,每一人都會面臨一個選擇,我們需要公開透明所有的資料,需要重建公道和正義。更需要喚醒人們的道德和良知,因為只有那才是人們唯一的出路。
主持人:好,非常感謝董宇紅博士。您說的這個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們看到中共政府還沒有接納美國的專家去中國,那我們希望能像您所說的,能夠有這種透明公開的資訊。另外我們也希望全球相關的科學家,醫學界的人士,更多地、更快地了解這個病毒的情況。那董博士我們希望有機會能夠請您再上我們的節目,就勢態的進一步的發展,請您再做解讀。非常感謝您今天和我們連線,謝謝您!
董宇紅:好,謝謝主持人,謝謝觀眾!
主持人:好,觀眾朋友也非常感謝您今天的收看。我們會持續關注這些事件,那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
📰支持大紀元,購買日報:
https://www.epochtimeshk.org/stores
📊InfoG:
https://bit.ly/EpochTimesHK_InfoG
✒️名家專欄:
https://bit.ly/EpochTimesHK_Colu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