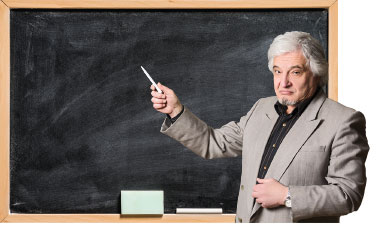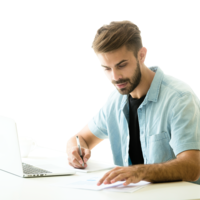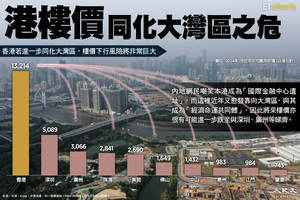我怎麼會想起迪‧薩米思教授呢?
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我始終認為我之所以大學沒有畢業,都是他害的。而我之所以被捲入這個局,都是因為我沒有大學畢業。還有就是安娜跟我結婚兩年後甩了我,按照她的說法,原因是她發現我是個有強迫症的失敗者,不知道我之前為了面子,跟她瞎掰了甚麼。
我因為懂德文所以沒有大學畢業。我奶奶是意大利北部上阿迪傑自治區的人,從小就讓我說德語。我上大學第一年,為了生活費開始接案子翻譯德文書,當年懂德文是能當正職工作的。可以看懂並且翻譯別人不懂的德文書(當時是很了不起的事),收入比法文翻譯高,甚至比英文翻譯高。我想就跟今天懂中文或俄文的情況一樣吧。
總而言之,翻譯德文書跟大學文憑二選一,二者兼得辦不到。既然翻譯是不管炎夏或寒冬都在家裏待著,腳上穿著拖鞋就能工作,同時還能學到一大堆東西,幹嘛要去大學上課?
我可有可無地決定選修一門德語課。我的盤算是,這樣我不需要花甚麼力氣讀書,因為德語我已經會了。當時負責那門課的是迪‧薩米思教授,他在一棟破敗的巴洛克風格大樓裏成立了學生口中專屬於他個人的「鷹巢」,走大樓梯上去之後會先看到一個寬敞中庭,一側是迪‧薩米思研究室,另一側號稱大會堂,這是迪‧薩米思教授誇大其辭,其實不過是可以容納五十人左右的大教室。
必須換穿室內拖鞋才能進到他的研究室。門口有為迪‧薩米思所有助理和二至三名學生準備的拖鞋,沒有拖鞋可以換的人就得在門口等。研究室內的一切都打過蠟,我猜就連書架上的書也不例外。包括那些從不知道多久以前就排隊等著拿到正式教職的年邁助理臉上,也彷彿打了一層蠟。
大教室有挑高穹頂、哥德式花窗(我始終不懂巴洛克建築為何會有哥德式花窗)和綠色玻璃。在某個時刻,正確來說是下午一時十四分的時候,迪‧薩米思教授會走出研究室,間隔一公尺跟在他身後的是最年長的助理,間隔兩公尺的則是那些五十歲以下——相對而言比較年輕的助理。年長助理幫迪‧薩米思教授拿書,年輕助理負責拿錄音機,五○年代末的錄音機體積龐大,簡直像一輛勞斯萊斯。
研究室和大教室之間的十公尺距離讓迪‧薩米思教授走成了二十公尺,他不走直線而是走曲線,不知道走的是拋物線還是橢圓線,一邊走一邊高聲說:「來了,我們來了!」進到教室後一屁股坐到一種石雕墩椅上,彷彿接下來的開場白會是:吾乃以實瑪利。
透過綠色玻璃照進來的光,讓他那張笑得不懷好意的臉份外蒼白。助理啟動錄音機,他開口說:「我與我那位可敬的同僚博卡多教授最近發表的看法意見相左……」然後滔滔不絕說上兩個鐘頭。
那道綠光讓我陷入昏昏欲睡狀態,從那些助理的眼神看來他們也一樣。我理解他們的苦。兩個小時結束後,學生蜂湧而出離開教室,迪‧薩米思教授讓人倒帶,然後他走下墩椅,親民地跟其他助理一起坐在教室第一排,把剛才那兩個小時的授課內容重聽一遍,每每聽到他認為關鍵的段落就心滿意足頻頻點頭。那門課談的是聖經翻譯,馬丁路德翻譯的德文版聖經。我的同學說那是個貪念過重、眼神呆滯的傢伙。
二年級下學期末,很少去上課的我大膽地說我的論文想寫赫姆‧海恩作品中的反諷(我覺得他處理不幸福之愛的手法固然寬慰人心,然而究其實,一切起因於他的憤世嫉俗,而我正準備迎接我的愛情)。
「你們這些年輕人啊,」迪‧薩米思教授十分不悅地對我說:「滿腦子只想投入當代研究……」
我忽然靈光一閃,明白了,頓時打消跟著迪‧薩米思教授寫論文的念頭。然後我想到費里歐教授,他比較年輕,以聰明睿智著稱,專攻浪漫主義時期及相關研究。不過學長提醒我,無論如何要請迪‧薩米思擔任第二論文指導教授,而且我不能公然跟費里歐教授走得太近,否則迪‧薩米思教授會立刻發現,然後跟我勢不兩立。
我必須用點手段,讓事情看起來好像是費里歐叫我跟著他寫論文的,如此一來迪‧薩米思教授會把矛頭指向他,放我一馬。迪‧薩米思教授討厭費里歐,因為當年是迪‧薩米思教授讓費里歐拿到正式教職的。大學(那個年代的大學,不過我想今天恐怕也一樣)跟外面的世界正好相反,不是兒子憎恨父親,而是父親憎恨兒子。
我心裏盤算著要如何利用迪‧薩米思教授每個月在大教室舉行的演講活動,假裝跟費里歐不期而遇,那個場合很多教授都會出席,因為迪‧薩米思總能邀請到優秀學者擔任講者。
結果事情經過是這樣的:演講結束後立刻開放聽眾發問,那是教師獨享的權利,然後大家散場,因為主辦單位要請演講者前往當地最好的烏龜餐廳用餐。餐廳是一棟十九世紀建築,服務生的制服是燕尾服。從鷹巢到餐廳得先走一條拱廊大道,穿過一個老廣場,在一棟被列為古蹟的大樓轉角處轉彎,再穿過一個小廣場就到了。拱廊大道上,圍繞在講者身邊的都是正職教授,一公尺外的是兼職教授,兩公尺外的是助理,合理距離外的是勇氣十足的學生。學生走到老廣場上就會停下腳步,走到古蹟大樓轉角就告辭的是助教,兼職教授會陪著穿過小廣場,然後在餐廳門口向大家告辭,會進餐廳用餐的只有貴賓及正職教授。
所以費里歐教授自始至終不知道有我這麼一個學生。這段時間我對念書已經失去興趣,再也不去學校。我當自由譯者接案,收入端看對方付多少,然後我一頭栽進一套新甜美風格的三部曲小說中,主角是倡導德意志關稅同盟的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不難想像為甚麼後來我不再做德文翻譯,想重拾學業卻又為時已晚。
問題出在我無法持續告訴自己,這樣一天過一天,遲早會修滿所有學分,把論文寫完交出去。一個人如果抱著不可能實現的希望而活,注定會失敗。但是必須等到某天他有所意識,才會放手。
剛開始我跑到瑞士恩加丁當家教,那個德國男孩實在太笨,沒辦法去上學。那裏氣候宜人,孤單程度在可忍受範圍,我忍了一年,因為薪水很不錯。然而男孩的母親有一天在走廊上貼過來,讓我明白她不介意獻身(給我)。她一口齙牙,還有淡淡的小鬍子,我很客氣地讓她知道我無此打算。三天後我被辭退了,理由是那個男孩沒有任何進步。
之後我開始應徵文書工作。原以為可以幫報社寫寫稿之類的,結果我只能棲身地方小報,撰寫鄉間表演活動和巡迴劇團的劇評文章。為了微薄薪水我寫過綜藝劇評論,在後台偷瞄打扮成水手的舞孃,看著她們的橘皮組織看得入迷,跟在她們後面到牛奶工廠喝一杯拿鐵充當晚餐,如果手頭還有一點閒錢,就再加一個奶油煎蛋。◇(待續)
——節錄自《試刊號》/ 皇冠出版公司
------------------
📰支持大紀元,購買日報:
https://www.epochtimeshk.org/stores
📊InfoG:
https://bit.ly/EpochTimesHK_InfoG
✒️名家專欄:
https://bit.ly/EpochTimesHK_Colu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