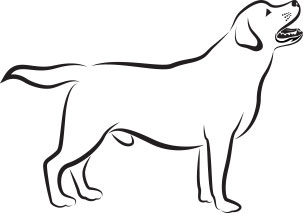為了騰出空間讓我能為她接骨,我忙著挖雪,小狗則唉唉哼著,兜著圈子走,然後爬上主人葛洛福的大腿,舔走他臉上的雪花。牠想知道飛機何時才起飛。
我空手扒一扒雪,只一分鐘就凍麻了,心想,空手挖不是辦法。我在葛洛福前面翻找,在機門的套袋找到一個夾紙寫字用的塑膠板,把紙拿掉,把塑膠板當成鏟子用。以板子鏟雪,動作快不起來,最後總算挖出夠大的一個平底坑,讓她躺得進去,方便我治她的左腿。
我抽走她身上的睡袋,在坑底擺平,然後抱著她,把她從座椅移進平底坑。我累垮了,索性挨著葛洛福的座椅坐著喘氣。我還不敢深呼吸,避免肋骨腔更痛。
狗在我身邊走來走去,蹦上我大腿,舔我的臉。
「喂,小子,」我低聲說。我忘記他叫甚麼名字了。
休息了三十分鐘,我才養足力氣,再去救她的腿。
我坐起來,對她喊話,但她不回應——這樣也好,因為接骨勢必比骨折還痛。
我抽出腰帶,一頭纏住她的腳踝,另一頭纏住我手腕,加強施力點。然後,我脫掉左腳的登山靴,慢慢把左腳掌放進她的兩腿之間。我把自己的腿打直,緊貼她的腿,接著束緊皮帶,雙手握住她的腳。
我深呼吸四五次,意識到她伸一手摸我的腳丫。我抬頭一看,發現她一眼半睜。她拍拍我腳丫,喃喃說:「用力......拉。」
我用腿推拉,拱背起來,動作一氣呵成。
一陣激痛貫穿她的腦門,她驟然向後仰頭,壓抑不住的尖叫聲含糊脫口而出,隨即喪失意識。傷腿鬆了,我轉它一下,讓它自然打直,然後放手。我的手一鬆開,左腿「癱」向一邊,姿勢還算自然,和右腿相仿。
治療腿骨折有兩大要領,一是接骨要接對位,二是固定傷處,以利斷骨癒合。兩者都不容易。
骨接好後,我開始找支架來固定。我頭上掛著兩根斷掉的機翼支架,長三英呎多,和我的食指差不多粗。左翼被撞斷時,機翼支架也被扯成兩半。我握著金屬支架折來折去,讓金屬疲乏,最後斷了。
登山時,我常帶兩把折疊刀,一把是瑞士軍刀,另一把是能固定的單鋒折疊刀。這兩把刀在機場安檢無法通關,所以被我收進背包托運,而背包目前躺在機腹裏,在我們後面,大部份被埋在雪堆裏,只露出一角。我撥掉雪,找到拉鏈,伸手進去摸索,兩把都找出來。
我這把瑞士軍刀包含一大一小兩支刀。我用小刀劃破艾許莉的褲管,從大腿割到腰。她的腿腫漲不堪,大腿大部份有烏青的現象,有些地方甚至呈深紫色。
兩座椅的安全帶都能從肩膀斜束身體,配備典型的快速鬆脫扣環。安全帶的束帶有兩條,我把安全帶拆下來後,以束帶固定我剛從機翼折斷的「棍子」,扣環雖然粗大,卻能給我鬆緊骨折支架的自由。我用支架包住她的傷腿,好好纏緊束帶,讓扣環壓在大腿骨動脈的正上方。
然後,我從行李取出一件T恤,割成兩半,緊扭成直管狀,接著把這兩管壓進扣環左右下方,減少動脈的壓力,讓傷腿有充份的血液循環,能促進復原。
被我這樣動來動去,她高不高興,我不清楚,但最後這步驟絕對會讓她痛恨我。我在斷骨周圍堆雪壓緊,以利消腫,卻又不至於讓體溫下降。
我再往背包深處摸索,找出一條聚丙烯衛生長褲,也找到一件我在山上穿的羊毛衣。這件羊毛衣有點襤褸,但裏面有一層防風織,即使毛衣溼了也能保暖。我脫掉她的羽絨夾克、褲裝的外套、上衣、胸罩,檢查她的胸部和肋骨,看看是否有內傷的跡象。
不見瘀青浮現。我幫她穿上我的衛生褲和毛衣,衣褲雖然大她幾號卻乾爽溫暖。然後,我為她穿回羽絨夾克,但不把她的手穿進袖子。我把睡袋鋪在她身體下面,把她裹成木乃伊,只有左腿外露。
接著,我把她的左腳墊高、蓋好。
人體有半數的體溫從頭部逸散,所以我從背包取出一頂羊毛豆豆帽,套住她的頭,向下拉,遮住耳朵
和額頭,露出眼睛。我可不希望她醒來誤以為自己死了或瞎了。
讓她乾爽溫暖後,我才發現自己的呼吸多淺、脈搏多快,肋腔也痛得更厲害了。我穿夾克,在她旁邊躺下來取暖。小狗一見我躺下,立刻跨過我的腿,原地兜兩圈,伸長鼻子找著尾巴,在我們之間做窩趴下。看樣子,他以前做過這種事。我望向另一邊,看著被雪埋葬的葛洛福。
在我閉眼的一瞬間,艾許莉的左手從夾克伸出來,手指碰觸我手臂。我趕緊坐起來,正好看見她的嘴唇嚅嚅動,但我聽不懂她想講甚麼。我彎腰湊近一些。她的手指捏捏我的手掌,嘴唇又動一動。
「謝謝。」◇(節錄完)
——節錄自《絕處逢山》/ 遠流出版公司
------------------
📰支持大紀元,購買日報:
https://www.epochtimeshk.org/stores
📊InfoG:
https://bit.ly/EpochTimesHK_InfoG
✒️名家專欄:
https://bit.ly/EpochTimesHK_Colu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