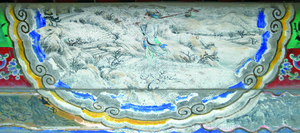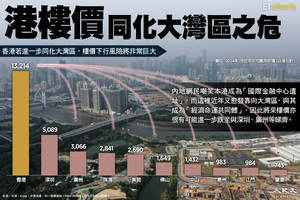講述人:李曼(倖存地主,1929年生)
記錄:譚松
(五)、李蓋五之死
李蓋五是我的堂祖父,比我祖父(李孟洋)小九個月。他是我們李氏家族最後一任族長,解放後他還立了功,在奉節縣當了統戰部長,土改時也把他抓來整,用鉗子把鐵絲捆在他頭上,還捆上一些爛棉花,然後淋上煤油來燒。整了好幾天,他最後是餓死的。
(六)、李盛槲妻子之死
李盛槲也是橫石村我們李氏家族的人,但他「解放前」(1949年前)已經死了。他的老婆姓劉,是嫁到李家屋的媳婦。土改時她50多歲,把她抓來鬥打。民兵問她想睡「軟鋪」還是睡「硬鋪」,她想到自己瘦,就回答說睡軟鋪。
農村有一種植物叫「火馬草」,這種草一碰到皮膚就火燒火燎地痛。於是,他們去去割了幾背篼「火馬草」來,然後把她脫光,幾叉叉子把她叉到「火馬草」上去,她痛得在上面打滾,那一滾後全身就胖了,腫起來了。接下來他們把她綁起,手腳都綁起,用火鉗夾起「火馬草」,一束一束地往她陰道裏塞。
當時沒整死,但是那個鮮血直流。她有一個過繼(抱養)的孫孫,有十七、八歲了,是貧農出身。民兵叫他把她背回去。在背回去的路上,她說「我想喝水喲。」她孫孫用角樹葉給她捧了一捧水,她喝了就斷氣了。
(七)、王大湜之死
王大湜是我媽媽王明淑娘家那邊的人,在土祥鎮梅魁鄉。那兒有一個王家大莊(園),那是一個文化集中的大家庭。大莊王家有10弟兄,是兩個媽生的。大媽是我們李家的子女,是我們的高祖母,嫁過去的。10弟兄中前五弟兄老大,老二、老三都是舉人、老四是拔貢(半個舉人),老五是秀才。後面五個,老六、老七、老八、老九我記不到名字了,他們都在土改前去世了。土改時只有老么還活著,已經是70多歲的人了。他叫王大湜,又叫湜老爺、么老爺。土改時也把他抓來整,那也是用了各種刑罰,一整幾個月呀。他要死之前是這樣折磨的。
先把他家裏的女人捆好,睡在地上,然後把他捆起,嘴就放在女人的生殖器上。女人撒尿時就要他喝,喝尿。最後把他翻過來,他躺在地上,把他的曾孫媳婦綁起放在他面上。他曾孫媳婦正好來了月經,一股一股的,他們強迫他喝。他喝女人的尿和月經,還多活了幾天。
湜老爺的後人,不知道有幾個,全部整死完了,只剩下一個,跑到黑龍江去了。
對了,就在那個王家大院裏,前後整死了幾百人,好像是389人,我寫的書上記得有。書記錄的是我們李家如何發家,土改如何敗下去,有20萬字。書被我兄弟拿去了,你現在看不到。
(八)、母子倆之死
我們這兒,整死的人多,有的一家一家的整死完。就我們洋沱壩,就有一對母子被整死。
有個小娃娃,把他媽抓來吊起,吊起後,他們把她才滿月的小娃娃抱來,用矛杆子從他肛門戳進去,那矛杆子有這麼長,戳進肚子裏面!這麼小的娃兒,他有甚麼過錯?他們把戳在矛杆子上的奶娃舉到他媽胸前,說:「你看喲,你兒子來親熱你了,他想喝口奶。」
他媽也死了,兩個都死了。
問:媽叫甚麼名字?
李:媽姓彭,我一下想不起了。
(九)、李先昭全家的遭遇
我叔叔李先昭住在離洋沱壩約30里的梅子園,當時與我們洋沱壩同屬一個村——橫石村(現在不是了)。土改時他家收多少擔租?嘿,收8擔租!他家還是有好大一壩田,為甚麼只收8擔呢?因為李先昭也是工商業者,他開得有酒廠,收入不靠田地,所以,農民種他的田最划算,農民交一擔租,自己要得十擔甚至十幾擔。土改時主要是逼他家的金銀。他全家有九口人,除了剛才講的李先昭和他大兒子李載承,還有6口人死於土改,他的二兒李宗列也是整死的,但我想不起他的死因了。特別是他的三個女兒,被整得最慘。
(當問到那幾個女兒,也是李曼的表姐妹是被怎樣折磨的,老人不願意談。最後,李曼老人終於開口說了一點。)
那些民兵實際上都是些流氓!共產黨就用這種人,土改時讓他們當了民兵,當了幹部。
他們把他女兒面朝下綁在板凳上,說金子就藏在她陰道裏,他們用手去挖她陰道裏面的金子。幹部也去,民兵也去,一個個跑去輪姦。奸了之後,他們說,這一下正好來打她的屁股嘛,就派兩個民兵站在兩邊掄起板子打她兩個大腿,把兩個大腿打得稀爛鮮血長流。打了後一看,地上有好大一灘從她陰道裏流出來的精液。
李先昭的三個女兒中有兩個(李載承的妹妹,李曼記不起名字了)在土改中被折磨死了,那些折磨的手法我就沒有看到了,是在屋裏整的。有一個才16歲,是個中學生。李載承的姐姐整殘了,神經失常了,她那年26歲。她也沒活多久,一年多後就死了。
他家九口人只剩下一個,就是李先昭最小的兒子,叫李宗沛,當時只有3歲。是同情他的人給他一口飯吃這樣他才活下來。李宗沛現在還在,而且還有後代。當年地主子女找不到老婆,後來他找了一個瞎子女人,那個女人給他生了兩女一兒,靠他一個遠房表姐的幫助,他們都上了大學,有兩個還留學國外,有一個還是個博士。
三、我的爺爺李孟洋
爺爺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同秋瑾等人在一起。他畢業以後回來,到成都熊克武手下做事,當時熊克武是四川省的都督。他幹了一段時間,覺得不適應官場,就告病還鄉回到洋沱壩。
我爺爺酷愛書畫,一輩子收藏書畫。他回鄉後修了一幢房子,農民叫花屋,有三層共九間,其中四大間全部用來藏書。他的藏書有七個方面的來源,我一時講不了。我們李家祖傳的書籍主要也在他這兒。
我曾經給那些書籍編目錄,僅目錄就編了四大本,每本有兩指厚。他的藏書中很有些大部頭,記得僅《佩文韻府》就有1800本。
字畫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條七、八丈長的白繪綾。白繪綾是日本產的絲織品,完全是真絲。那是我祖父留學日本的一個紀念品,上面有幾百人的題字,最前面的一首就是秋瑾寫的。她的字比其他人的字大。我很喜歡她那個的字,所以背下來了,現在我還背得到一部份:
地球面積為舞台,五色民族各一派,
太素元素作帷幕,精神腦力為器械,
鬥智鬥慧鬥新奇,刁鑽狡獪眾稱快,
或和或戰或悲歡,意態分明演百般,
但知日日登場好,那曉天公冷眼看。……
問:其他題字的是哪些人你曉得嗎?
李:曉得,以前我全部背得,現在一下背不到了。
土改的時候,工作組的人(裏面只有一個人識字)說這些書畫是封建毒素,要徹底粉碎封建毒素,因此,天天派人來背書去燒。
我很心痛,想阻止,結果被抓去鬥打,他們沖我吼:「這些舊意識的東西,這些反動的東西你為甚麼要珍藏起來?!」
所有的書畫都燒乾淨了,前後燒了五、六個月,光紙灰都挑了幾百挑,挑去肥田了。
白繪綾沒有燒,農民沒見過,以為是布。他們把它撕來分了,拿回去縫成褲子,女的穿起來開會我還看到的。
我爺爺死在燒書之後。土改時我家裏已經沒有甚麼財產了,爺爺是個讀書人,不善經管,修房子又花了些錢。我爸爸李仲達抽大煙,敗了家,分家到另一個村去了。他們把我們抓去整主要是追逼金銀。
問:追出些金銀了嗎?
李:哪裏有喲?沒得呀,只是從挖墳裏挖到一小點。但是玉多,都是從墳裏挖出來的。我們家族被挖了幾百座墳,全部挖完。他們挖苦說,李家墳埋得好喲,請風水先生看喲,結果挖得一個不剩。
土改那年(1951年)雨多,雪也大。我爺爺被關在一個石房子裏,又凍又餓,餓了兩三天,最後把他丟在一個石頭壘的巷子裏,他就死在那兒了。那是1951年的冬天,他68歲。
當時我已經被關押在村上的農會裏,爺爺在屋裏躺了幾天後,他們把我放回來埋他。
你想去看?看不到了。他的墳被人挖了。我們這兒認為,母豬病了,要用人骨頭燒成灰來喂,小豬要餵得肥,也要人骨頭去餵。於是有一個人(他的後人現在還在)就把我爺爺的骨頭挖出來去賣錢,治母豬的病。
採訪時間:2016年8月11日、8月13日
地點: 湖北省利川市柏楊壩鎮水井鄉水井村(原奉節縣橫石村洋沱壩)
採訪後記
2006 年8月,我到湖北利川採訪當年李氏莊園的土改幹事向賢早先生時,就聽他說,在李氏八大莊園建築中,洋沱壩的雕飾最為豐富。他還告訴我,李氏家族有個著名學士叫李孟洋,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醫學博士,他有很多書,土改時全部被農民燒了。
十年後,我在製作土改紀錄片《血紅的土地》時,專程到洋沱壩去拍攝外景。
洋沱壩在著名的大水井李氏宗祠下面10多里的地方,比較偏僻,路也很爛。到達一條小河邊時,我向橋邊一個小屋裏的老人問路。沒想到,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就是李孟洋的長孫李曼!
老人一直住在利川社會福利院,當天剛好被家鄉的一位朋友接回老家小住。他只比我先到達兩個小時。
冥冥中一定有神靈的安排,他彷彿是專程回來等我的到來。他等了65年!
他在他孤寡人生的遲暮之日,用清晰的語言,講述了六十多年前那驚心動魄的一幕!(全文完)◇
注:李曼老人在我採訪他之後9個月(2017年5月)去世。
------------------
📰支持大紀元,購買日報:
https://www.epochtimeshk.org/stores
📊InfoG:
https://bit.ly/EpochTimesHK_InfoG
✒️名家專欄:
https://bit.ly/EpochTimesHK_Colu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