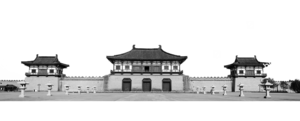這時明月緩升,華光滿地,天宇一片通明,窗外屋樹皆著銀霜,醉仙仍然在酣睡之中。
李承德突然問我:「天民老弟,屆時你也入社,怎樣?」
我說:「我還沒有入門,詩詞懂得很少。」
他又說:「到詩社裏學,不是很好麼?」
我一想有道理,便應允道:「那好,到時只要各位長兄不嫌棄我,我經常來學,好麼?」
劉朗突然自言自語,說:「叫『紫竹苑詩社』怎麼樣?」
李承德說:「我們靠近紫竹苑,雖紫竹隱有高風亮節之寓意,但不如取個近水的名字。叫『昆明湖詩社』怎樣?取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之意。我們離昆明湖不遠,那裏山水極佳,取這個名字表明我們愛仁愛智。」
劉朗問我:「天民,你以為怎樣命名為好?」
我沒想過此問題,只得敷衍道:「叫『精華詩社』怎麼樣?各位兄長皆飽學之士,各人有各人的拿手專長,將來必能造益天下,這類人匯到一起,叫『精華社』不是名符其實麼?」
劉朗說:「這個名字太直了,而且好像有些政治含意,要不得!」
就這樣,不覺已經午夜,我抬頭一看,月懸中天,萬樹肅靜,冷寂中月華如清水。我告辭了他們,至馬路邊候車。約半小時,無車,站牌下有三、五人與我一樣,凍得發抖。
我決定步行取暖,於是便踏月而行。一路雖寒冷割面,但因交了許多新朋友而格外高興。一會兒回味一天的見聞,一會兒駐足,遙望幽暗寂靜之田野。忽見路邊一叢無名樹木,枝上綴滿小花,隱隱雅淡,或紅或白,香氣徐飄,不禁止住腳步,輕聲自言自語:
「久別南方樹,今逢此地芳。
月落郊荒寂,人行興緻昂。
淡雅香黯立,明清氣靜涼。
不敢高聲語,恐驚枝上凰。」
自我回味了一番,深感自己功力太淺,僅憑火車上跟巴桑大哥學的那點常識,不足以達盡心中感興,甚至想到吟花不如看花,上前幾步,細看那滿樹花朵。不知何時,一陣冷風吹落數枚花片,也吹覺我返校之心。於是我小跑步回到了北京師大西北樓239宿舍。
***
開學後不久,我收到巴桑大哥的來信。其中提到了那位我還沒有見過面的回族大哥馬健行,在甘南老家因急性闌尾炎不幸喪命。信中約我於三月十四日下午至昆明湖某玉帶橋頭碰面,參加他們的詩社聚會。
三月十四日下午,天氣極佳,明晴萬里。我準時走向約定的聚會地點。遠遠望見巴桑大哥與一群男女青年聊天。我想:他們一定在指點江山,尋找詩興。又一會,連他們的笑聲也聽得清楚。
我悄自一數,發現有十三人,當我走近時,巴桑也發現了我,立刻上來拉著我的手,對大家說:「這是天民老弟,蘇北漢人,我們的特約佳賓。」
我有些不好意思,只是嘻嘻一笑,向在場的人表示友善。
然後,巴桑向我介紹其他各位同學,說:「劉朗,醉仙,李承德,李夫子,你早已認識。」
另外一一指點他人說:「他叫『馬剛』,回族,武威人;她叫『步木真』,蒙古人,滕格爾老鄉;她叫『王雯麗』,與費雯麗只差個姓,川南人;她叫『唐英』,苗族,苗好仁老鄉,貴州人;她叫『楊雪貞』,白族,大理人;她叫『金喜』,又叫『金芙蓉』,滿族,吉林人;她叫『徐文』,侗族,湘西人,名字像個男子;她叫『古麗』,新疆維人。
除了你早先認識的,新朋友與你都同級。將來我們畢業了,你們仍有許多機會相聚,真是個好緣份。」
巴桑說話時,我隨他手勢打量幾位新友,那馬剛,矮壯,神情持重;那步木真,中等個,短髮,四方臉,單眼皮,看上去,沉靜而敦厚;那唐英不到一米五,清瘦,雙目黑而亮;那楊雪貞大約一米六五,圓臉微胖,明眸皓齒,與電影《五朵金花》中的角色一樣漂亮;那金喜,身材高大,面黑而發亮,精神飽滿;那王雯麗,細高挑,雙目大而明亮,似秋水沉靜,若寒潭深邃;那維族姑娘古麗簡直像個西方的小影星;那徐文一臉活潑,猶如春花迎露,身材嬌小。
幾個人除了步木真與王雯麗看上去約三十歲外,其餘都是十八、九歲的樣子。
巴桑介紹完畢,領大家朝南邊漫步一段行程之後,我才知道巴桑的室友有幾人不願參加詩社,便介紹一些老鄉進來。 滕格爾介紹了步木真,苗好仁介紹了唐英,這兩個人又將她們的同學馬剛、楊雪貞、金芙蓉、王雯麗、徐文介紹進來。◇(待續)
------------------
📰支持大紀元,購買日報:
https://www.epochtimeshk.org/stores
📊InfoG:
https://bit.ly/EpochTimesHK_InfoG
✒️名家專欄:
https://bit.ly/EpochTimesHK_Colu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