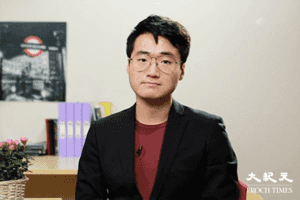這裏以前是撤軍時丟棄炮彈的地方,羅應貴像是拔蘿蔔那樣把它們拾起來,等待政府不定期地前來回收。
羅應貴和卸下了木墩的一位越南母親羅廷熊坐在窩棚裏,用苗語慢慢地聊著天,也不急於交易。
他們同姓同輩份,是認交的乾姊妹。跟隨母親前來的女兒,羞澀地迴避去了附近村長王和熊的窩棚裏。
王和熊的窩棚也是一處交易地點,幾個越南人卸下了檑木之後在窩棚裏吃著飯。
這些檑木是越南人從深山裏用電鋸盜伐,躲過本國邊檢站背負而來。如被抓住,一次要罰款人民幣兩千元。
中方邊檢站也嚴查走私,王和熊昨天被罰了款,這些越南人今天有些姍姍來遲。
兩人慢慢地聊著天,似乎都不注意離灶台不遠的石坎上,兩個像灰撲撲的醬醋瓶立著的東西。
「這是六○迫擊炮彈。」羅應貴事後說。
炮彈引信拆掉了,火藥還在。
如果這間窩棚失火,檑木垛子燃燒起來,最終這些沉睡的砲彈也將被喚醒。
窩棚腳下坡地的石頭上,遠近或立或擱著另外幾發炮彈。這裏以前是撤軍時丟棄炮彈的地方,羅應貴像是拔蘿蔔那樣把它們拾起來,等待政府不定期地前來回收。
上一次回收已過去兩年。
通往村子的小路邊,羅應貴挖了一個「地窖」。撥開濃密的腐草和浮土,臥著兩百多枚迫擊炮彈,它們失去了鋼鐵的觸目顏色,像是越冬的蘿蔔。但其實它們只是在冬眠,死亡在彈殼下保存得好好的。
「肉麻吧。」羅應貴說。
更讓人肉麻的是小路上下的地雷,有草叢的保護色,像嗅覺靈敏的小動物,時刻等候人的腳步。穿過界碑的小路,是兩邊走親戚販菜板的人在雷區硬趟出來的。
到羅應貴窩棚裏來賣菜板的羅廷熊,有六個兒子,一個在三歲時被炮彈貫通前胸死去。在她住的一百多戶人的村子裏,被炮彈炸死的有五個人,地雷炸傷的也有五個。
小路通向的八里河村,是雲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縣天保村民委員會的一個邊境村落,村子頭頂是一九七八年開始的對越自衛反擊戰主戰場東山,和著名的老山主峰隔河相對。
戰爭結束已經二十四年,村裏一戶人家的屋前,標有型號的彈藥箱裏長出了蔥綠的蒜苗。
但更常見的情形是,一個完好的上身連著假肢。在鄰近的馬鞍山寨楊成方全家福照片上,七個人中有三條假腿,兩隻殘腳掌,一隻失明的眼睛和一雙被震聾的耳朵。
沿中越一千多公里國境線伸延的這些村落,被稱作地雷村。戰爭雙方撤退之後,地雷成了最終的佔領者。
根據資料,三次政府組織的掃雷行動,大約只除掉了當初埋設的一半,僅麻栗坡縣就尚有五十萬顆地雷。
回到村莊的農民像陷入包圍的士兵,用鋤頭和身體打著另一場戰爭,重建家園。到處是帶有骷髏標誌的禁區牌子,像昨天剛剛樹立。
九月七日是收穀子的天氣,正午繁忙的村莊一片寂靜,所有的傷殘或者健康人都離開了屋子。
稻田裏分不清打穀子和割穀子的腿腳中,哪些是假肢,哪些是真的。休息時人們撩起褲管,才顯示出上下身的差別,讓人把眼前這個和平的小村莊和外界說的「地雷村」關聯起來。
國產的塑膠假肢在人體上顯得刺目,似乎一個人的生存被強行嫁接了虛假的一部份。但又似乎比其餘的一切更真實,就像地雷村成了這裏天生的名字。
在這名字之下,執著生活或者無聲死去、消沉或勵志的故事都同樣過剩。勇敢和膽怯一樣自然,像地雷炸響之時的疼痛和麻木,在一個人體上同時發生著。
二○○三年,攝影師盧廣第一次來到八里河村,這個兩百零八人的村落有一百餘人被地雷炸傷,炸死十一人,三級殘廢以上四十六人。
鄰近的馬鞍山寨共一百六十九人,二十八人被炸傷殘。傷殘數位逐年都在變動,部份傷口感染者死去,每年又有新的觸雷者,二○一一年馬鞍山寨和八里河各增加了一名肢殘者。八里河村現存九人失去腿腳,馬鞍山寨有四人截肢,兩人眼睛失明,近年來已有三位肢殘者死去。
根據二○○四年民政部門的一份資料,整個麻栗坡縣因戰造成傷殘死亡人員一六百七十六人,其中殘廢兩百五十一人(肢殘兩百二十四人)、死亡五百五十四人。傷殘亡年齡最小的五歲,最大的八十一歲。
塑膠雷的報廢期是一百二十年,邊境線上未排除的地雷約有一百萬顆。這意味著地雷村的故事雖然已被講述了很多遍,卻只是剛剛開頭。◇
——節錄自《青苔不會消失》/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
📰支持大紀元,購買日報:
https://www.epochtimeshk.org/stores
📊InfoG:
https://bit.ly/EpochTimesHK_InfoG
✒️名家專欄:
https://bit.ly/EpochTimesHK_Colu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