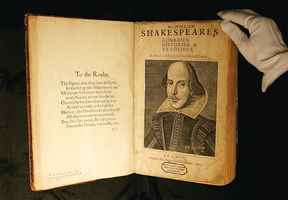少年時期的馬克思是一名受洗的基督徒。步入大學後,在時代浪潮的不斷衝擊下,再加受到青春期內心危機等因素的影響,馬克思原有對上帝的信仰很快便土崩瓦解,沒多久,昔日虔誠信神的馬克思就變成了一個與上帝不共戴天的瀆神的馬克思。
許多人只知道成年後的馬克思是個有名的無神論者,對宗教始終持敵視和反對的態度,他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的著名論斷,為共產黨國家打壓宗教奠定了理論基礎,也可以說是宗教信仰在這些國家遭受迫害的苦難之源,但他們卻不知道,上大學前的馬克思也曾是一名信神的虔誠基督徒。
馬克思出生和成長在一個富有宗教氛圍的家庭和社會裏,父母都是猶太人,雙方都是有著濃厚猶太教傳統的家族的後代。兒子出生後,馬克思的父親為了避開國家對猶太人從事法律事務的限制,方便從事法律工作,選擇做了一名新教徒,並在公元1817年8月之前受了洗。
公元1824年,馬克思也受洗做了一名基督徒。在這種環境中長大的少年馬克思,對上帝有著與一般基督徒相同的虔誠信仰自然是不足為奇的,而最能夠證明這一點的是他本人寫於公元1835年夏天的一篇畢業作文──《根據約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節論信徒和基督的一致,這種一致的原因和實質,它的絕對必要及其影響》。
他在作文中寫道:「人是自然界唯一達不到自己目的的存在物,是整個宇宙中唯一不配做上帝創造物的成員。」儘管我們每個人的心裏都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熱情、求知的慾望、對真理的渴望,但是慾望的火焰經常會把永恆的東西的火花吞沒,罪惡的引誘會淹沒我們追求美德的熱情,生活的威力也會嘲弄這種熱情,貪圖富貴功名的卑鄙企圖會排擠我們求知的慾望,虛偽的甜言蜜語會熄滅我們對真理的渴望。正因為如此,我們才需要與基督一致。
馬克思的這篇作文得到了他的老師約瑟夫‧居佩爾牧師的稱讚。遺憾的是,跨入大學校門之後的馬克思很快走火入魔,背棄上帝,成了一名無神論者,對自己原先的信仰大加撻伐,並由此漸漸走上創立和宣傳共產主義、禍害人類的歧途。
走上歧途
根據現有的資料,我們一時很難確定馬克思從一個有神論者轉變為一個無神論者的準確時間,但在寫於公元1836年左右的〈願望〉一詩中,他已直言不諱地宣布了與上帝的決裂。這種決裂實際上也是他與神的決裂──因為受基督教的影響,在歐洲,人們談到神,多半都是指上帝。
馬克思在這首詩中寫道:
精神於我何有,天堂算什麼?空空!
你,只不過是永無結果的一個夢。
要知道,蘊藏在我胸懷裏的一切,
不知時間為何物,也不知道天公……
———
如願意,你就去供奉上帝──
你已經從他的內部站起,
你不能夠使我同他和解,
我和他已經永遠揚鑣分離。
從上述詩句的內容來看,馬克思之所以決定與上帝「永遠揚鑣分離」,是因為在他看來,上帝也好,天堂也好,都不過是「一場空」,「是永無結果的一個夢」。換句話說,此時,他已徹底否定了上帝和天堂存在的真實性。
儘管所有的無神論者都否定神的真實存在,但他們並不一定仇恨神。可以說,那些既不信神又仇恨神的人,不是一般的無神論者,而是極端的無神論者,馬克思便是這樣的典型。
在〈暴風雨之歌〉中,馬克思寫道:「我在打破所有的鎖鏈,我要向萬里長空飛翔,我燃燒著烈焰般的激情,要把全世界緊緊擁抱。」然而,讓他備感受挫的是,他的身體成了他「靈魂的鎖鏈」,頭頂的天空束縛了他的思想,「到處都給人世間的生活,設置了不可逾越的界限。」這種挫折感激起了馬克思對創造世界的上帝的滿腔怒火,他咬牙切齒地詛咒上帝道:
你,上天,塌下來,塌下來,
我願意同你一起垮臺,
我願自己永遠地成為,
壓成碎片的一堆殘骸。
當我快進入死神之國,
我定要向上帝與生活,
送上我最痛恨的詛咒……
更準確地說,馬克思不僅是一個極端的無神論者,而且是一個戰鬥的極端無神論者。
天堂是上帝創造的「永恆之鄉」,背棄上帝後的馬克思一心盼著它的毀滅,並把這一天視為自己「甜蜜的瞬間」。他在〈願望〉中懷著滿腔仇恨寫道:
難道我一定要委身於一個信念,
壓在他的下面,生活在黑暗之鄉,
不惜用大千世界和天堂來發誓,
要信誓旦旦,永遠不變,天人共見?
算什麼?你那漫漫的永恆的旋轉,
還有這個令人難堪的永恆之鄉?
我將要在你的毀滅的懷抱裏面,
去享受一下死亡的甜蜜的瞬間。
在馬克思成為激進的青年黑格爾派的一分子後,攻擊有神論、批判人們對上帝的信仰,一度更是成了生活中他最關注也最起勁的一件事。
布魯諾‧鮑威爾是青年黑格爾派中反對宗教的領軍人物,也是馬克思當年最親密的朋友。公元1841年3月起,馬克思還曾計劃與鮑威爾一起創辦題為「無神論卷宗」的評論,它將以鮑威爾的福音批判為基礎。對此,馬克思的另一位朋友盧格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這樣評論道:「布魯諾‧鮑威爾、卡爾‧馬克思、克利斯提安森和費爾巴哈正在形成一種新的『蒙太涅』,正使無神論成為他們的格言。上帝、宗教、永恆被從它們的王座上推下來,人類被宣告為上帝。」
大學畢業後,馬克思的關注點開始從宗教轉向社會政治,儘管如此,他對神的敵視態度卻終生未變。
成魔之路
有人推斷,青年時代的馬克思曾加入過撒旦教。不管這種推斷最終能否被證實,馬克思身上的魔性卻是顯而易見的,那是一種糅合了仇恨、毀滅、暴力、陰冷與瘋狂等因素,並且包裹著惡的內核的混合物。
馬克思就讀柏林大學時,老馬克思曾在一封信中不安地告訴兒子:「你的前途,你要在某一時候成名的這種值得讚許的願望,以及你當前所處的順境,——這一切不僅是我記掛在心上的事情,而且也是我內心深處早就珍藏著的幻想……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證,即便這些幻想成了現實,也不會使我感到幸福。只有當你的心始終是純潔的,它的每一次跳動都是真正人道的,任何一個惡魔都不能把你心中比較高尚的情操趕跑,──只有那時候,我才會得到我從你那裏夢寐以求的幸福。否則,我將看到我一生最美好的目的被毀滅。」
顯然,想到愛子的心靈可能落入魔鬼的掌中,老馬克思不禁憂心忡忡。從前一段話看,他不僅肯定此時馬克思的心裏已經有了個魔鬼,而且認定它已主宰了馬克思的一切,只不過這魔鬼究竟是「天上的還是浮士德式的」他尚不清楚罷了。事情就像馬克思主義者弗蘭茲‧米哈林在《卡爾‧馬克思》一書所說的:「雖然卡爾‧馬克思的父親在他兒子20歲生日之後不久就死了,但他似乎已隱隱覺察到,他喜愛的兒子是魔鬼。」
老馬克思的這種擔憂並非杞人憂天,完全是事出有因。因為在馬克思當時寄給他的大量詩歌習作中,非但屢屢出現魔鬼的身影,而且明確表露出了對它的認同和依附。下面這首〈小提琴手〉就是個再確鑿不過的證據。
小提琴手撥動琴弦,
淡淡褐髮垂額間,
腰佩長長的寶劍,
身披寬寬的皺褶衣衫。
「琴手呵琴手!你為何奏得如此急切?
為何你怒目環視?
為何你熱血沸騰?
琴手呵!你可要把琴弓摧折!」
「何必問我如此拉琴?請看一看海在咆哮!
它衝向巉巖,聲若驚雷,擊得粉碎,
我也要拉到雙目失明,胸膛迸裂,
讓靈魂沉入地獄,帶著餘音迴旋!」
「琴手呵!你冷嘲熱諷揉碎心,
英明的上帝賜予你的藝術,
你該把它化作樂曲飛上九天,
讓它伴著燦爛群星舞翩躚!」
「什麼話!我要把這血污的長劍
直插在你的靈魂心間,
是上帝不懂也看不起那藝術,
它從冥冥地獄爬進頭腦裏面。」
「我從魔鬼那裏買來這生機勃勃的藝術,
它使我魂飛心醉。
魔鬼為我擊拍還用粉筆譜曲,
我得如痴若狂演奏死神進行曲,
我得日日夜夜拉琴,
直至弓弦使我腸斷肝裂。」
小提琴手撥動琴弦,
淡淡褐髮垂額間,
腰佩長長的寶劍,
身披寬寬的皺褶衣衫。
熟悉馬克思早年詩作的人都知道,與「歌手」和「船夫」等形象相同,馬克思在寫詩時也常用「小提琴手」指代自己,因此這首詩其實就是馬克思的自畫像。按照詩中馬克思對自己的描繪,他演奏的不是上帝賜予的「飛上九天」、「伴著燦爛群星舞翩躚」的「樂曲」,而是從魔鬼那裏「買來」的、從「冥冥地獄爬進」自己「頭腦」中的「死神進行曲」。更重要的是,魔鬼不僅為他「擊拍」,還用粉筆為他「譜曲」。儘管「上帝不懂也看不起」這曲子,它卻讓自己「魂飛心醉」、「如痴若狂」。可見,此時的馬克思已完全拜倒在魔鬼的腳下,猶如被它附體了一般。
在〈歌手的愛情〉裏,馬克思則頗為柔情地吟唱道:
不是他不想嚐到幸福,
不是他不想得到平靜,──
而是他心中的激情澎湃奔騰,
命中的魔鬼催趕他走向征程。
這個「他」顯然指的並不是別人,而是馬克思自己。「魔鬼」不但讓他「激情澎湃奔騰」,而且「催趕他走向征程」。如此聽命於「魔鬼」的召喚,說明馬克思的意志已被它主宰。
來自朋友的印象也印證了這一點。到柏林大學讀書後,馬克思加入了崇尚「批判」的青年黑格爾博士俱樂部,並很快成為其中一名活躍的中心人物。埃德加爾‧鮑威爾是該俱樂部領路人布魯諾‧鮑威爾德的弟弟,也是俱樂部的成員。他曾在一首詩中這樣描寫當時的馬克思:
「是誰風暴般地奮勇前行?
一位自由魔怪,來自特利爾的黝黑身影,
似乎想要抓住天空使它匍匐在地,
他自信的步履敲擊著地面
震怒的雙臂直指蒼穹。
他似乎千萬惡魔攫住身體,
攥緊可怖的拳頭狂奔不停。」
可見,在埃德加爾‧鮑威爾眼中,當年的馬克思純粹就是一個被「千萬惡魔攫住身體」的「自由魔怪」。
無獨有偶。大學畢業後,馬克思在波恩加入了科倫社團。這個社團的核心人物格奧爾格‧榮克也曾是柏林博士俱樂部的成員。在科倫社團中,他很快成為馬克思最為親密的朋友。他也曾向人介紹說:「馬克思博士是一位革命魔鬼。」(待續)◇
------------------
📰支持大紀元,購買日報:
https://www.epochtimeshk.org/stores
📊InfoG:
https://bit.ly/EpochTimesHK_InfoG
✒️名家專欄:
https://bit.ly/EpochTimesHK_Colu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