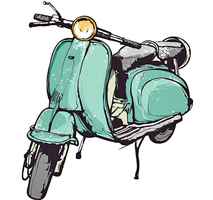樓上祖孫吃的米是爺爺在世時的積穀打的,烤的木炭是爺爺自己挖窯燒的,灶屋門外垛滿的柴禾是爺爺砍的。爸爸離開之後,似乎爺爺還待在這間木屋裏,用餘力照料了奶奶和楊軒。
父親開始在家幹活打短工,楊軒大一點後出門下礦。
前年底傳來了他在冷水江出車禍的消息。一個吸毒的人徑直撞上了爸爸的摩托車,爸爸當場身亡。
臥房裏的一疊卷宗裏,保存著爸爸在太平間的遺照,腫大的頭部凝結著血痂,旁邊標註著「顱腦重度損傷致死」的法醫鑑定。
重傷的肇事者一貧如洗,無力賠償,最後當地政府補償了兩萬塊錢,自家把爸爸的遺體拉回來下葬,沒有剩下甚麼。
爸爸的猝然離開,撤掉了家裏最後一根柱子。這之前四年,爺爺已經積勞死了。爺爺過世的那天,幹了一天活回來,晚上腦殼痛,上床躺一會,就再也沒醒來。醫生說是腦溢血。
奶奶覺得爺爺是累死的。樓上祖孫吃的米是爺爺在世時的積穀打的,烤的木炭是爺爺自己挖窯燒的,灶屋門外垛滿的柴禾是爺爺砍的。爸爸離開之後,似乎爺爺還待在這間木屋裏,用餘力照料了奶奶和楊軒。
爸爸在世時沒有能為楊軒攢下甚麼。
「他也不誠實,喜歡打牌。」奶奶說。
雖然如此,楊軒知道爸爸走了生活就不一樣了。
「爸爸在時比現在好。」
好在哪兒,她仍舊茫然,但明白自己和別的孩子有點不一樣。以前就不一樣,現在更不一樣了。
「我想爸爸了。你也想爸爸了。」有次她對著奶奶說。
奶奶想念的除了爺爺和楊軒爸爸,還有早年死去的大兒子。奶奶一共生了四個仔,結紮後又生了兩個,國家要她去再次結紮。奶奶當時腰有病,強行結紮之後,腰就再也直不起來了。
「家裏窮,給大兒子治病花光了。」
大兒子有小兒麻痺,好不容易養到二十幾歲,爺爺、奶奶背著去懷化看病,終究還是早早過世。
兩個兒子先後過世之後,奶奶的心臟出了毛病,加上腎病和風濕,需要三天兩頭吃藥。去年春節奶奶說周身痛,楊軒的大叔叔買了一些藥回來。
今年大叔叔說不回家過年了。他從學校畢業後就很少回來過,也沒錢寄回來。
「他的學白上了,花冤枉錢。」鄰居和奶奶一起感嘆。
大叔叔上的是江西一所專科學院的民族預科,以後又到陝西漢中上學,讀的心理學專業冷門,又有些駝背,就業困難,還欠下了幾萬塊助學貸款,輾轉在外打工,一直沒有成家。他的工資「四個月還不到一萬塊」,自用後無甚剩餘。
小叔叔以前在家,去年年初也出門打工。鄰居說他人有點遲鈍,在福建建築工地上當小工,一月工資只有千把塊,也無錢寄回來。
小叔叔過年會回家。楊軒更想念的卻是很少見面的大叔叔,時常拿著畢業相冊在上面尋找。
「他不打人」。
小叔叔卻脾氣暴躁,經常打楊軒耳光。楊軒的手背上有兩條微微凸起的傷痕,自己忘了是何時留下的,只餘驚惶的神情在眼中閃動。
家裏的日常收入是楊軒和奶奶的兩份低保,加上奶奶的老年保險。奶奶的摺子鎖在爺爺留下的舊黃銅鎖皮箱裏,上面密麻麻打滿了存錢和取現的紀錄,最大一次的金額是五百元,最近的帳戶餘額則是十七元。
最固定的開銷是楊軒的寄宿生活費,儘管有免費午餐,早、晚飯最便宜的仍要七元,一月下來要將近二百元。爸爸在時楊軒一周有十元零花,現在變成了一兩塊,也不是每周都有,用來買本子和筆。
圈裏小豬沒有錢吃補鈣補血的營養粉,但摻抗生素的米粉仍舊要錢。田裏零星種的糧食菜蔬要買肥料。更大宗的支出則是鄉鄰人情往來,祖孫倆沒有鄰居幫襯,在鄉土深處是難以維生的。
最近學校有元旦文藝匯演,讀三年級的楊軒也想報名,老師說:「妳就不要參加了,跳舞的衣服要七十元。」
楊軒糾正奶奶,說:「是七十二元。」
爸爸在的時候,楊軒參加過幼稚園舞蹈演出,穿著五十元一套帶褶的裙子。
如今爸爸買的衣服都還是好的,楊軒卻穿不上了。身上的外套是鄰居送的,褲子是鄰居家姐姐給買的,毛線塑膠底鞋子是坎下另一家鄰居給織的,裏面穿的紅毛衣則來自一位天津的「愛心媽媽」。這位愛心媽媽通過新晃的一個公益組織聯繫上楊軒,每年補助楊軒一千五百元學習花費。
這位愛心媽媽還曾想收養楊軒,因為相隔太遠不知底細,奶奶又離不開楊軒而作罷。有時祖孫兩人爭嘴,楊軒會說:「我自己去天津。」
現實中,楊軒最遠跟爸爸到過新晃,見過一次火車。
「嗚嗚地叫,很好看。」
奶奶只好抹眼淚。有時楊軒看著奶奶塌著背蹣跚的樣子,會在後面撇嘴模仿,鄰居大嬸就教育楊軒,不能嫌棄、欺負奶奶:「你們是相依為命。」◇(待續)
——節錄自《青苔不會消失》/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
📰支持大紀元,購買日報:
https://www.epochtimeshk.org/stores
📊InfoG:
https://bit.ly/EpochTimesHK_InfoG
✒️名家專欄:
https://bit.ly/EpochTimesHK_Colu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