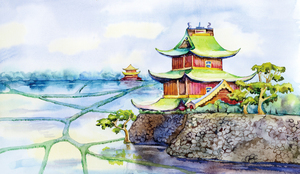結婚那一年,岳母把出租的一間房子要了回來,讓我們住進去。
這是一個侷促在嘉義市鐵路後站的古老聚落,零零落落地居住了幾十戶人家,曲弄小巷蜿蜒纏繞,每家每戶前門後院隨意錯落,外人來到這裏鐵定找不到出去的路,十足是個哄亂的大雜院,一般人都叫這裏「北港車頭」,正式的名稱是長安里,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
我們搬進來那天已經接近中午,我進進出出忙著指揮工人時,聽到大腳嬸在巷子轉角處遠遠的拉高嗓子,喝斥著一群橫衝直撞的孩子:「人家在搬東西,不要亂跑。」待整理就緒以後,我站在低矮的屋簷下擦著汗水,看到坐在菜擔子旁的大腳嬸,歪著脖子打盹,一片石灰牆遮擋了斜射的陽光。
原來大腳嬸一年到頭總是赤著腳到處晃盪,才得到這個稱號的,這是隔壁賣粉圓的阿勇告訴我的。阿勇住在我的隔壁,家裏只有一個七十幾歲的老母,早晨天未亮,他就乒乒乓乓的把我吵醒,我惺忪著睡眼走到門口,總會看到他彎著腰正在往手推車裏的爐子添加木炭,鍋裏冒出來的煙霧,貫滿整條巷弄,一陣陣粉圓的香味飄盪在空氣中。
晨曦悄悄地攀上大腳嬸家褪了色的門聯,這時她也拉開了門板,大剌剌地咳了兩聲,一隻蹲在簷下瞌睡的公雞咕咕地飛了起來,兀自闌珊地走開。大腳嬸跨出門來,踮起腳跟把兩柱香插在門楣上;天漸漸亮了,一群戴黃色小帽揹著書包的小學生,唧唧喳喳地從阿勇的推車前跑過去。阿勇推起車子,拉開喉嚨:「燒粉圓。」老母急急忙忙從屋裏趕了出來,把一件厚衣衫披在阿勇背脊上。
阿勇快三十了還找不到老婆,可急壞了老母,當著老母的面,大腳嬸常數說阿勇:「我隔壁攤賣布那個阿枝仔,人家長得也不錯,個性乖乖的,只是你們阿勇沒有意思。」阿勇一天到晚總是推著車子大街小巷叫賣粉圓,平常不大講話,晚上吃過了飯,他會獨自躺在門前的籐椅裏聽收音機,我問他聽甚麼節目,他告訴我說:「聽講古啦,廖添丁傳奇。」
記得有一次我跟妻子在屋裏看電視,忽然燈暗了,阿勇抱著收音機探進頭來:「變壓器壞了,我去廟口電器行買,馬上回來。」阿勇兩下子就把日光燈弄好了,屋子裏恢復了光明,這時,我看到他手裏揣著一瓶啤酒,轉身鑽進屋裏去了。
黃昏時,陽光從西邊媽祖廟屋脊上那對剪黏飛龍鋪過來,小巷裏好像穿上了金黃色的衣裳,阿火伯面東那堵磚牆更顯得褚紅,牆上竹竿晾曬的衣衫在晚風裏飄盪著,放了學的學生一隊隊從巷口蹦了進來,各自回家去了。
點了燈以後,孩子一個個端著碗跑到巷子裏,一面扒飯一面嘻鬧著,這時大人儘管自己在屋裏忙著煮飯或做家事,可不管他們了,阿火伯有時會站在磚牆邊端著煙斗,在煙霧裏看著這群活蹦亂跳的孩子。
在這裏住了一年多之後,一晚,妻子肚子痛了起來,我攙著她準備去醫院,在巷子裏給大腳嬸撞上了,她瞧著妻子的肚子說:「肚子這麼大了,要小心一點,需要甚麼就叫我。」我們在巷口等的士時,大腳嬸還站在巷子裏望著我們。
我在醫院產房外待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太陽還沒出來孩子就出生了。我飛奔回去,氣喘吁吁地敲著大腳嬸的門,她慌張著臉問我:「生了?」我喘著氣:「生了。」她吆喝了兩聲,一群人都跑出來了,她們圍著爐子,一會兒工夫就弄好了一鍋什錦麵,裏面還浮著兩個荷包蛋。我提起鍋子要上醫院時,大腳嬸才拉著我的手問我:「是男的還是女的。」
孩子出生沒多久,我向銀行申請貸款買了房子,就離開了北港車頭。
去年岳母因為退還公家宿舍,自己搬進去住,還是滿熱鬧的,她在電話裏告訴我:「大腳嬸在問你啊。」
那天我跟妻子提著一簍蘋果去看岳母,在巷子口就看到了大腳嬸,陽光裏一個人坐在矮櫈上,皤白的頭髮飛散著。我正要趕過去招呼,她還是原來的個性,瞇著眼先開口了:「你找誰啊?」
大腳嬸已經不認得我了。◇
------------------
📰支持大紀元,購買日報:
https://www.epochtimeshk.org/stores
📊InfoG:
https://bit.ly/EpochTimesHK_InfoG
✒️名家專欄:
https://bit.ly/EpochTimesHK_Colu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