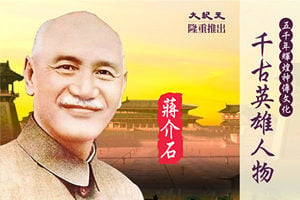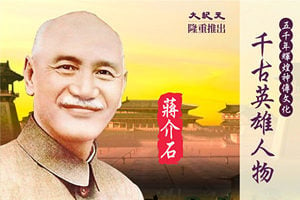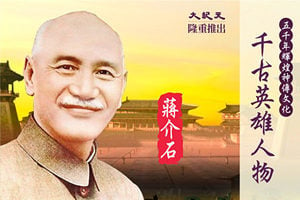在京都一家日本料理店吃飯,服務生是來自大陸的留學生,上菜時她皆能以中文解說各是些甚麼菜。吃至尾聲,閒聊間問她:「你們伙房開飯,都吃些甚麼飯菜?都吃得慣嗎?」
「吃得很慣,只是有時會很想吃家鄉菜,像番茄炒蛋之類的,結果跟大廚說,他就做了。」
「做得怎樣?」「哇,很好,蛋炒得嫩極了!」
原來這日本大廚原本就每天做玉子燒(煎蛋捲),對於蛋的質地與油的多寡、火候的掌控早就深諳,再試著對番茄有他做廚子的透徹洞悉力,像番茄的含茄沙程度、溼滑性之處理等,馬上便能將兩者結合得非常好。
也就是,從來沒做過某道異國菜的廚子,只要他有做菜的敏銳概念,往往亦可有驚人之筆。
反觀我們坊間的番茄炒蛋:炒得疙瘩肥鈍坨坨塊塊的有之,炒得番茄生脆脆的有之,炒得整盤油兮兮的亦有之,而自助餐店自作聰明勾芡又擱些微糖的,更是教人啼笑皆非。
老實說,一盤恰如其分的番茄炒蛋還不見得好找呢!
許多食物是可以跨國界的。倘一個日本老陶藝家或老匠師在他的工作室接待訪客,恰好到了午飯時間,而他常在中午自己做漢堡吃,於是便以漢堡饗客,搞不好這漢堡比太多的名店還好吃呢。
意大利有一小鎮,叫Reggio Emilia,夾在Parma和Modena這兩個名鎮之間,鎮上有一中型旅館叫Notarie,旅館樓下的餐廳,菜燒得極好極靈巧,有一次中午吃它的簡餐,是炒飯,售8塊5毛歐元,以小小几片火腿(prosciutto),幾片襯托式的芝麻葉,用橄欖油淺淺炒成,便是一盤好飯。
他炒得不像中式炒飯,也沒有弄成他們製燉飯的稀糊半生那種風味,就只是一盤既不油、又不過乾、過脆、且完全是天生理解飯與油與食材相處於一道的靈性作品。
蓋房子亦如此理。
陪著幾個西洋來的建築師逛看蘇州園林,像網師園啦、獅子林啦、拙政園啦、留園啦等等,看完閒聊,我問他們,如果在現代蓋類似明、清這種意趣的房子卻一點也不管它們的雕琢、不管宗法制度下的形制格式,甚至不管工匠的高難度技藝的木作,只恪守簡單本質之原則,還能夠蓋出教中國人與西方人同樣讚歎的優質房子嗎?
大夥意見各有不同,最後皆指向一個觀念:好的又簡單的房子,不論是東方人蓋或西方人蓋,蓋好了各國人一看鹹道「這就是所謂的好房子」時,便即成矣。
東方人無意學維多利亞式房屋,亦學不像。西方人無意學明清式房屋,亦學不像。倘在更細緻的層面,像西方人學書法,很難習臻中國人的那種靈動精妙。於是,何不化繁就簡?就像是日本人習中國拳法,極妍巧極繁瑣之動作很不易普遍習得盡像,然改成合氣道簡化版,卻心法步法等原則不變,亦能極有效果。
民初的營造學社,即使建西式樓宇,亦加上中式簡易框、頂、架勢,照樣不錯。如北京的協和醫院等。日本近代化廣建西式樓房,卻在東方形式之和融上做得極好,不只辰野金吾等幾個人而已也。
武漢大學的校舍,是西洋結構之上覆以中式圖案頂飾極成功的例子,尤其自遠處望去,特別呈現巍峨卻又不失文雅氣勢。
廈門的集美,有愛國華僑陳嘉庚(1874-1961)自1913年起出資糾工陸續蓋成的小學、中學、大學等一大批樓房,這批校舍固也是西洋結構加上中式肩頂眉宇,然它們甚有「邊做邊調」的素人情致,流露出深富生命動線的筆觸,人在遊觀時會不自禁的被某些轉折處吸引,而多停在那兒琢磨一陣,甚而生「陳嘉庚何許人也」之讚,這是很美趣的經驗。
竊想有一種情形,陳嘉庚的器識塑形了他想蓋出房子的格調。
怎麼說呢?陳氏顯然不是建築師,卻見過西洋的真房真樓,亦在其中過過佳美日子,又一意深愛自己中國的屋舍格律,真要下手建築他心中覺得合於長久時宜的房子時,終會流溢出他胸中沉吟良久的好模樣。
可見器識與胸懷,才真正是建築最緊要的東西。
孫中山在翠亨村的故居,也同樣透露這股味況,雖然他只是後來返鄉稍稍增建了一小部份,同時設計添建燒柴火的洗澡熱水器而已。
孫中山周遊極廣,十九世紀各國的佳相常在心中縈繞低徊,不只是蓋房子、吃飯等閱歷而已。若說設計中、西人皆宜穿的衣服、中、西人皆適合展閱的書籍裝幀、甚至中、西人皆適合安坐的椅子,搞不好他皆能有過人的見解。只不過他的主業是革命,是救國。
器識,或說眼光,真是很重要的能耐。
當然,器識並不全然在於出國,更在於對身邊諸事之隨時寄情、因地觀照,與自己援引之取捨。◇
——節錄自《雜寫》/皇冠文化出版公司
------------------
📰支持大紀元,購買日報:
https://www.epochtimeshk.org/stores
📊InfoG:
https://bit.ly/EpochTimesHK_InfoG
✒️名家專欄:
https://bit.ly/EpochTimesHK_Colu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