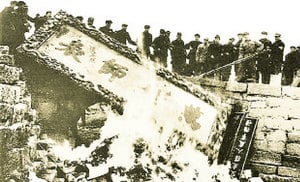就這樣,那一夜我遭到這夥暴徒的毒打,皮鞭、棍棒雨點似地落在我前胸、後背,我憤怒抗議,高聲呼救,但都沒用。這審訊室是外語系的專業錄音室,隔音能力超強,室外的人根本無法發現屋裏有人慘遭蹂躪。
將我痛打一番後,這群暴徒還嫌不過癮,想出更加刺激的一招:8個壯漢分成兩班,輪班站在錄音室的四角,一人一拳把我從一端痛擊到對角線的另一端。不消幾拳我就被擊昏。暴徒們並沒有就此罷休。他們潑水將我弄醒,測試我的脈搏後發現我心跳仍屬正常、抗擊打能力「了得」,不禁喜形於色,商量著如何進一步施虐。我知道這夥暴徒早已喪失最起碼的人性,今晚不把我折磨個半死決不會善罷甘休。「仕可殺而不可辱」,乘他們為如何繼續折騰我而爭論得熱火朝天之際,我掙扎著奔到門邊,打開緊鎖的室門,衝到陽台口縱身跳下樓去。
相信是天意,我居然沒有死,只是左腿大腿骨縱向骨折,流了很多血,被送往醫院急救。救護車的呼嘯聲驚動了整個師大園,紅四團未經團部、師部批准對「反動學生」刑訊逼供的醜聞迅速傳遍全校。為洩憤,周建平等打手迅速趕赴醫院急救室,企圖將我置於死地,但被醫院造反派制止,最後悻悻離去。
同晚,另一名「黑幹將」、第一醫學院的女生鄭曉萌亦因同樣原因跳樓自殺未遂,牙床粉碎、臉部嚴重變形、一條腿粉碎性骨折,人只剩最後一口氣……
血腥「鎮反」後,我們32個「反動學生」(除了已被開除學籍、押回原籍監督勞動的外語學院畢業生周森根)被定性為「階級異己分子」,即政治上的「賤民」,只能老老實實接受改造;稍有不服,任何人都可以施以精神摧殘和肉體迫害。
批鬥升級
1968年8月,中央文革針對「階級鬥爭新動向」,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鬥爭,千百萬平民百姓被指控為「牛鬼蛇神」,遭到殘酷批鬥和肉體摧殘。「上海大專院校紅衛兵聯合鎮反兵團」再次進駐磚橋,對過去一年中我們32名「反動學生」的反動言行進行批鬥。
凡不滿現狀、發過一些牢騷、說過一些錯話、怪話,甚至只是些俏皮話的,諸如「搞修正主義的吃麵包,搞馬列主義的吃窩窩頭」、頭頂空熱水瓶,嘴上說「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水平(瓶)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說說看,朱元璋為甚麼炮打功臣樓」(涉嫌影射毛澤東排除異己、打倒一大批建國有功的老將軍、老高幹),都是這次紅衛兵打擊的對象,被罰跪、鞭韃,被罰相互打耳光,甚至被吊在屋樑上用馬鞭猛抽。
機電專科的徐錚因對我們中的一位女生萌生愛意、寫過幾封情書而觸犯了「兩勞期間嚴禁談戀愛」的改造紀律,被紅衛兵吊在打穀場邊的那棵老槐樹上毒打一頓;因拒絕認「罪」、悔改,又被五花大綁推到公路邊、跪在公廁旁,整整一天不給吃喝,出手之毒辣,手段之狠毒,令人髮指。
朗朗乾坤,公義何在?天理何在?
發配農村務農
1969年夏,毛澤東指示:「對被批鬥、清算的人員要落實政策給出路。」形勢逼著上海市革委會教衛部對我們這批超期「服刑」的「兩勞」「反動學生」進行組織處理。當時,全國各地市革會有關部門早就將管轄的「反動學生」調回各自所屬院校處理,絕大部份受害者都得到體面的出路安排,就地就業。唯獨上海市革委會教衛部例外,因為害怕上級領導翻舊帳、追究其對青年學生處理過當的責任,遲遲不予啟動對我們32個同學的安置工作。
同年秋季,為解決城市人口惡性膨脹、無業閒散人員越來越多的問題,中共中央提出「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的口號,指示把大批無業閒散人員驅趕到農村安家落戶。上海市革委會教衛部瞅準這個絕佳時機,藉口執行中央指示、落實政策給出路,給每個超期「兩勞」的學生作解除處分安排:除個別「改造尖子」回校報到、分配工作之外,我們絕大部份「兩勞」學生被開除學籍,作為無業人員送回個人所屬市區,由各區上山下鄉辦公室統一安排,與閒散人員(絕大部份是四類分子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一起送到安徽農村安家落戶。
我左腿致殘,只是勉強能行走,根本無法以務農為生,要求給予照顧,留在上海市區就業,但被一口回絕,因為對我的政治結論是:「罪行嚴重且抗拒改造,屬敵我矛盾性質,暫不戴帽(即帽子拎在群眾手裏,如拒不悔改,隨時可以戴上),交群眾監督勞動,以觀後效,赴安徽農村安家落戶、以務農為生。」萬般無奈,我唯有接受,否則我無法存活於世。
1969年底,我與其他12位上海籍難友就這樣被分別驅趕到皖南、皖北農村落戶。家在外地的難友統統被趕回原籍,自謀生計。不論是去安徽農村的還是回原籍的,個個謀生艱難,如無父母接濟、親友照顧,連溫飽也難以維持。
華東紡織學院的姜大維回老家後,被下放農村十餘年,後來被上調常州老家,謀得一份為雜貨鋪拉板車送貨的工作,竟欣喜若狂,千恩萬謝給他介紹這份工作的「恩公」。
我在安徽農村幹了兩年農活後,有幸被生產大隊聘為民辦小學教師;太太跟我在同一大隊落戶,在大隊裏做赤腳醫生。夫婦倆都拿大隊工分,不用下田勞動,羨煞生產隊的小青年,我聽了唯有苦笑和感嘆:「小子們哪!你們哪裏知道,如果不是當年那場冤獄,我本當在大學講堂上給學生講課,或著書立說、考研經商。」
與我相比,好幾位難友的境遇可謂悲慘至極,令人唏噓。機電專科的徐錚,在長達6 年的改造生涯中飽受折磨虐待和人格侮辱,被送回浙江老家後不久就患上肝癌,因沒有勞保沒錢治病,病情迅速加重,最後全身浮腫,病入膏肓,含恨與世長辭。
第二醫科大學的老右派封育都因老家無人,被校方踢來踢去,硬是不給安排出路,最後精神失常,送醫後不久便突然逝世。
最早被開除學籍、遣送回鄉交群眾監督勞動的外語學院畢業生周森根在家鄉生活了幾年,靠養豬種菜為生,精神病時好時壞,反覆無常,不幸英年早逝,臨終時喃喃自語:「我是主動交代的,為甚麼……」他沒能把話說完;我知道他想要說的是:「為甚麼要下手這麼狠?」或:「為甚麼不給我一條生路?」
尾聲
告老退休後,我曾單獨赴磚橋,對老難友說,這算是我謀劃已久的尋蹤之旅。自當年「發配」磚橋勞改至這次舊地重遊,間隔40載;磚橋面貌已改換一新,我根本無法辨,這裏曾是我和其他32位難友們蒙難服刑的「兩勞」基地。
原來的「兩勞」宿舍早已按當時市革委會指示全部拆除(大概是為了掩蓋他們曾在這裏殘酷鎮壓「反動學生」的滔天罪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穀倉。當年季兄被紅衛兵毒打,頭破血流,鮮血染紅了打穀場一隅;如今,打穀場已經過徹底翻造,血跡無處可尋。
唯有打穀場邊的那棵老槐樹依然屹立在那裏。當年在它的樹蔭下,在那場批鬥「反動學生」的群眾大會上,紅衛兵曾血腥鎮壓無辜的學生。機電專科的徐錚僅因寫過幾封「情書」就曾被綁吊在它那粗壯的臂膀上遭毒打。
我相信,它一定樂於向走過樹下的每個人、我們的每個子孫後代,講講60年代中後期的一天晚上在這裏發生的暴行,讓他們知道當年年輕學生所遭受的劫難其實是異議中國知識份子命運的縮影,我們的經歷是對那個時代痛定思痛的反思與見證。(全文完)◇
------------------
📰支持大紀元,購買日報:
https://www.epochtimeshk.org/stores
📊InfoG:
https://bit.ly/EpochTimesHK_InfoG
✒️名家專欄:
https://bit.ly/EpochTimesHK_Colu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