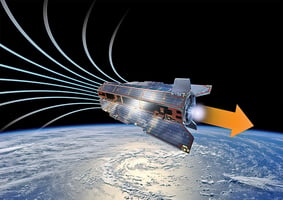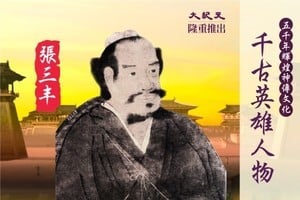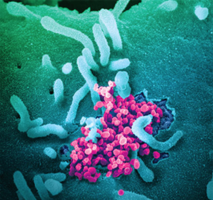千古以來,詩人遙想嫦娥一人在遙遠而冰冷的月裏忍受曠古的孤寂。事實是在皎潔的月裏,永生的嫦娥,忙於挖掘她埋沒了太久的創造熱情。沒有人知道其實她非常忙碌。
雲朵移過天幕,纏住了嫦娥的腳。她的腳和她纖細的臉不相稱,十分的骨感而有些過長。身子失控了一般,嫦娥朝天穹飛去,把塵世的重量一絲絲卸下。
羿的身影小了,腳下的火球一一跌落,不覺中,大氣生出了變化。雲彩從天的巢穴移出來,在天邊泅泳。空氣清涼起來,稀薄起來。億萬星系在她的腳邊、指尖閃爍,向敻遠展開。嫦娥裹在一下下撲打的絲袍中,無重量地穿過璀璨的星辰,一如鳥兒飛過叢林間翠玉的葉子。她透明的眼瞳,一雙發光的琥珀在松石綠、寶石紅、普魯士藍的星辰間閃爍,凝視沒有窮盡的蒼穹——它慷慨而又廣大,殊勝而又美善,遠遠,遠遠超出她的想像力,叫她熱淚盈眶。
對於嫦娥赫赫有名的奔月之旅,人們所關心的、茶餘飯後好奇地猜測經久而不衰的,是她居心叵測的動機。甚麼叫她放棄地下的幸福,跑到無人的星球上一個人待著?做為神射手羿的妻子她有甚麼不滿足?羿射下來的山裏的獸,天上的飛鳥烹出的野味難道不夠鮮美,填不飽她的胃?那些個吃不完的鹿肉啊、貉腿啊,想想都要叫人垂涎三尺,她卻一走了之?她果真是個不計後果的女人?拋下羿——更主要的是,偷了羿的不死藥,豈是件小事?那不是犯了女人的天條?這樣的女人該大大懲戒一番。
嫦娥抵達月球之後的事,人們並不關心。直到現在,沒有人一語道破真相:她是一名遠古洪荒的創建者。千古以來,詩人遙想嫦娥一人在遙遠而冰冷的月裏忍受曠古的孤寂。他們為她居住的月宮取了個名字:廣寒宮。一想到那孤獨而寒冷的,冰雕的巨殿,足以叫他們從心底打個寒顫。毫無疑問,她受的懲罰是人難以承受的,是絕對的。
事實是,在皎潔的月裏,永生的嫦娥忙於挖掘她埋沒了太久的,創造的熱情——她在地球上一直無法發揮的創造力。沒有人知道其實她非常忙碌。在月球上,她做的第一件事是建築棲身的地方。從月山腳下鑿下巨冰、玉石,一塊塊砌出透明的「廣寒之宮」。又從火星、水星、冥王星上搬來顏色瑰麗的岩片,砌成一間巨大而堅固的工作室。冰牆上,她雕出一幅幅奇異的畫像、山水;岩壁上,她拿礦石繪出色彩繽紛的圖畫,橫跨了整面牆。
透過冰牆上的窗櫺照進來熱烈的星系,和牆上的畫像相呼應。隨時間而變化的星辰旋轉對位,照在畫像上,使人像露出了不一般的神情;在特殊的時刻,當星球之間獲得了獨一無二的角度,星光照入了畫中人物的眼瞳,折射出奇異的光彩,對她說奧秘的,如同音樂的話語。庭院中,她植下金星上移來的奇樹、金字塔,樹冠在殿上投下抒情的影子。
嫦娥不是隻身一人。這在她剛剛抵達月表時就發現了。她穿越大片蒼穹來到月球;腳還沒觸地,一頭雪球般的長耳兔子磨蹭著,牠冰冷而厚重的長毛輕觸嫦娥的腳,像是月兒在對她致意。這頭渾身雪白的兔子是哪兒來的?牠獨自一人在這月表上待了多久?這些都是不必要的問題。有人畫下藍圖,叫這頭乖巧的小獸在孤寂的月上等待嫦娥,給這屬於女人的神話添些有趣的,溫暖的細節。
於是這頭怪好玩的,冰毛披了一身,圓敦敦的「玉兔」成為嫦娥頑皮的助手。牠滾著叫人疼愛的身子在她身邊跑前跑後,一會兒端來硯墨,一會兒端來畫筆、顏料,歪頭看嫦娥手下一筆一筆出現的,奇特而繽紛的圖象,圓圓的紅眼睛瞅著嫦娥,眼裏盛滿了動物天真而又深沉的困惑。
有時候,玉兔鉤起長長的,軟軟的耳朵拂嫦娥的腳,提醒她,該給月兒洗刷洗刷皎潔的身子了。
這玉兔還有一個任務。牠立起身子,前腿拿石杵一下下把藥石和著各色異草的根莖搗碎。肥白的、毛絨絨的腿夾住石杵,頭歪向一邊,一隻長耳朵垂下來,牠那認真的模樣時常叫嫦娥忍俊不住,偷偷笑了出來。在這神秘的藥屑裏,她放入了綠色的香氣和繽紛的記憶,使這藥生出了奇妙的功效,雖然很少人知道這藥到底是做甚麼用的,更少人知道這藥的名字。
在光怪陸離的月表,嫦娥開始了女人永不止息的創造日。◇
——轉載自《新紀元》周刊
------------------
📰支持大紀元,購買日報:
https://www.epochtimeshk.org/stores
📊InfoG:
https://bit.ly/EpochTimesHK_InfoG
✒️名家專欄:
https://bit.ly/EpochTimesHK_Column